为何极端天气会让我们觉得“爽”?

来自风暴的奇怪祝福
当一只鹿朝着我狂奔而来,一根松树枝从我头顶飞过,我很确定这事不太对劲。天色很快变暗,远处传来类似火车呼啸过森林的动静——声音先至,随即迎面扑来猛烈的风浪。树木被吹得朝一个方向整齐弯曲,然后又弹回来狠狠打在紧挨的树上。
我开始应接不暇,巨大的卷轴云层层叠叠,被闪电紧紧捆扎成一堵沉重的云墙,直接掠过西弗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小镇,翻涌着蔓延过阿勒格尼山脉。蓝天映衬着锋锐的云峰,与其说这是一种天气,倒不如说像是抽象派画家罗斯科(译注:美国抽象派画家。生于俄国,10岁时移居美国,曾在纽约艺术学生联合学院学习)的作品。我曾经在这个偏远的小镇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正和往常一样,在从我家到我所工作的国家射电天文台的路上跑步。肾上腺素告诉我,我得再跑得快一些。

我在12分钟内跑了两英里,这是一段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我也从未经历过的旅程:一路需要跨过许多被风吹倒在路中间的电线杆和树木。好在我意外地安全回到了家中,随即牵着我的狗来到了农舍的地下室避风。经历了令人不安的30秒之后,我又作死回到楼上,打开门站在门廊上。城墙一般的飓风狠狠拍打在我的身上。闪电如同频闪闪光灯一般狂闪不止。我开始清醒了,我还活着。云层继续向前推进,这股狂暴的力量似乎清洗了空气,给整个世界打上了黄色的灯光。
我并不是第一个体验和尝试用文字描述这种极端天气的人。沃克·珀西在他于1966年出版的小说《最后的绅士》中就曾有写道:“他觉得,所有人都和他一样,认为此时此刻还不如呆在飓风里。”现在,人们在各地的天气预报节目中用交叉手指的方式来表示暴风雪将会加剧。雷雪天气往往会使人们感到头疼。珀西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小说家,也曾被这种气象所吸引。在他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早期随笔中,他问道:“当人们置身于舒适环境中时,为什么会感到糟糕,置身糟糕的环境中却感觉良好?”
为什么飓风可以让你从连你自己都可能没察觉的情绪低潮中挣脱出来,变得情绪高涨?这对于哲学家,小说家,包括哲学和小说的爱好者而言,都将是个说不尽的话题。而这个现象本身也会因我们自身而放大——破坏性带来的罪恶感将会蚕食我们的理性,而对自己的反感使得我们对这些极具破坏力的现象喜闻乐见。
但是风暴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心理层面。一门名为生物气象学的科学正在试图解释大气的变化对生物体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总的来说,这门科学研究的主题大体包括季节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农业对气候的依赖,以及天气是如何传播或者抑制人类疾病的。几十年来,其中一个方向的研究人员甚至提出一个理论:被风卷起在空气中的离子将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对环境作用于人类方面的解释,有时候会让你感觉这压根儿就是伪科学。带电离子影响人类的理论直接导致了一些存在争议的医疗方式出现,比如空气负离子疗法。话虽如此,最近一项严谨的研究却暗示了离子、生理与心理三者之间神秘的关系。
上世纪中期,离子发生器和离子测试仪技术日渐成熟,业界标准也愈发完善,科学家们开始尝试解读因环境和天气作用而散布至空气中的离子和人类心理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自然产生,还是在装置中人工制造出来,离子的电属性都是一样的:负离子多了一个电子,正离子缺少一个电子。当空气摩擦地面或者撕裂水滴的时候,不显电性的分子被剥夺了一个电子。而这个电子会在一番辗转之后吸附到氧分子上,使得后者变成了一个负离子。
在盛夏或者潮湿的野外,空气中往往富含这种负氧离子,人们会感到愉悦。从天而降的雨水和击打在暗礁上碎裂开来的浪花,都在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负离子。闪电也是如此。而正离子则往往依附在烟、霾、粉尘等污染物上,通常出现在室内,都市里,还有冬天。而像加州的桑塔利亚飓风那灼热干燥的暴风雨前锋,也会带来正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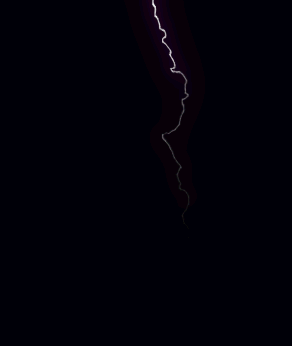
闪电如同频闪闪光灯一般狂闪不止。我开始清醒了,我还活着。
新奥尔良州的医学博士丹尼尔·西尔弗曼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的科恩布鲁,是最早探测天气中离子浓度变化对人类身体与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的科学家。影响结果会是完全意义上的积极或者消极?还是中性?1957年,他们对实验者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人造电子接触实验。
实验期间,西尔弗曼和科恩布鲁通过脑电图观察了实验者的脑电活动。不管是只被负离子,或者正离子,或者两者同时(此处暂不明确)充斥的环境中,实验者绵长而缓慢的α型脑电图看上去平缓而放松。另一个研究组后来也证实,当实验者接受负离子作用时,他们的大脑活动会相对轻松,感觉会愈发敏锐。尽管他们的结论并不确凿,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进行的另外三个研究,都揭示了电子是如何影响人类感知自我状态(舒适和不安)的过程。比照这个实验,有些研究得出结论:正离子产生消极情绪,有些则声称负离子会使人产生积极情绪。
这些模糊不清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了一项普遍的认知:正离子有害,不仅会助长犯罪率,还会引发哮喘,使人变得易怒。而负离子则帮助你变得更快乐。但是这些实验本身在证明这些论点哪怕其中一点的过程中,都缺乏说服力。研究人员所做的全是混乱的实验过程,不规范的测量和存在问题的实验变量控制。
1981年至1987年期间,又相继出现了13项关于电子的精神效应的研究。其中11项都声称得到了明确的实验结果,且结论导向:正电子有害,负电子有利。而同样由于实验对于剂量的把控,过程的设计和变量的控制都存在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得出一个保证正确的结论。

即使电子真的会改变我们的生理状态,科学家至今也不清楚它们的作用原理。A.P.克鲁格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E.J.里德以及希伯来大学的菲利克斯·苏曼提出了一个在某一时期普遍被接受的理论——5-羟色胺假说。他们声称,正离子会产生大量的5-羟色胺(一种神经递质,可理解为化学信使,通常与感知快乐、愉悦的受体相关)。但是高浓度水平同样会引发问题——我们后来称之为“5-羟色胺刺激综合征”。根据作者所言,正离子将增高血液中的5-羟色胺浓度。而负离子为了恢复浓度的平衡,会从神经递质上剥夺下这些由有机分子组成的胺,令5-羟色胺浓度恢复到正常水平。
而其他的科学家认为5-羟色胺假说存在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科临床心理学教授米歇尔·特曼是最近正在从事关于电子的研究的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指出:“所谓的5-羟色胺假说所关注的是血液浓度。”但是血液中的5-羟色胺产自内脏器官,而大脑中的5-羟色胺则来自大脑本身。特曼表示:这是两个渭泾分明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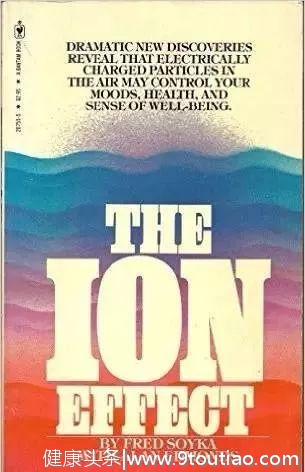
1983年,有个名为弗雷德·索伊卡的商人
开始设计“好离子”与“坏离子”的一套说法,
并出书《离子效应》,在当时引发热潮。
而正如很多科学家所预料的,一个更大问题出现了。1983年,有个名为弗雷德·索伊卡的商人开始设计“好离子”与“坏离子”的一套说法,并出书《离子效应》,在当时引发热潮。毫无疑问,此书成为了一些以negativeionizers(离子创造者).net或者negativeiongenerators(离子制造机).com等网址出现的团伙的圣经,而这些网站背后往往是那些大力兜售离子制造机并四处传播“离子治百病”类似言论的公司。对此,特曼说道:“当科学家正在寻找清晰而明确的真理时,流行的空气离子功效论让我们很尴尬。”
1987年,乔纳森·查理和罗伯特·卡维特将已有的相关大学论文整理成册,撰名《空气离子:关乎心理和生理》,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此时已经缓缓进入了瓶颈期。总的来说,30多年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实验结果往往互相矛盾,科学家也没有给出多少的生物学相关解释。前景似乎很不明朗。根据暴露量评估和剂量重建指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威廉姆·巴利对已有实验结果所做的元分析来看,1987年到1993年只有少数的相关调查研究。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实验开始展现出对空气离子的兴趣,类似于特曼所做的事情也在开始引导巴利和他的团队开始重新翻阅相关的调查文献,而据他本人所言,这距离上一次较大范围对空气离子相关研究的整理回顾已经有20多年了。
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生物节律科与光治疗之心的首席医师特曼,其实最初并没想成为一个空气离子领域的研究人员,亦或企图找出一个细小微粒会对人体产生的生理效应。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他的工作始于一次离子治疗:在另一组实验中,他将离子作为实验安慰剂。为了测试高强度的光照是否有助于抵制沮丧的情绪,他的实验需要一个参照组——一组既没有接受光照,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参照组的实验者。但是有个问题难以避免——大多数人都能看到光,所以参照组的实验者如果没有被光照射,就会知道自己接受的是安慰剂,而这有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的科学性。

于是特曼找到了曾经在一个相似的实验中用一个断电的离子发生器作为实验安慰剂的科学家——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拉里·查特和查曼尼·艾斯特曼,来共同讨论这个问题。那时,拜《离子效应》一书所赐,大多数人们都听说过负离子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心理状态良好。查特和艾斯特曼认为他们只有脱离离子发生器,但同时又要让他们以为离子发生器正在运行,人们才会相信他们正在接受正确的治疗(从而达到参照组的标准)。而特曼的做法有所不同:他仍然开着负离子发生器,但是把功率降低到了可以视为安慰剂的程度。这样一来即使参照组没有接受治疗,他们也宁可相信自己正被负离子友好对待。
随后,他比较了高光照射组、作为安慰剂出现的低功率离子环境组和高功率离子环境组。“就我个人而言,我其实并不指望高浓度的负离子环境可以明显减少消极情绪表现。”他说,“我本以为高功率组和低功率组最后会成为相似的对照组。正因查理和卡维特的整理工作出版之后,这个方面的实验工作实质上已然荒废,所以我对早期的一些著作中的相关结论保有怀疑。”
清晨的阵雨,或者暴雨,可能有抗抑郁功效。
但是实验结果令他感到了震惊。当实验者经历了30分钟的高浓度负离子实验的三周之后,抑郁症状减少了超过50%,而低浓度离子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这表明一个切实存在的生物反应正在高浓度离子组的实验者体内进行,就像吃更多的泰诺来缓解疼痛一样(尽管如此,巴利仍然提醒道,从元分析的结果来看,更长期或者剂量更大的频繁高浓度供给是不会产生更好的结果的)。
特曼将其结论发表于《替代和补充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中,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般发表了较为主流或者高影响力的内容:“其实你可以看出我对这一说法仍然保持谨慎。”随后,他又将此结论发表于《大众精神病学档案》杂志(现在的《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分册》)和《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中,而后者是业界内最有权威性的杂志。
而大众仍然对这种情绪变化的原理表示不解。 虽然说,5-羟色胺假说仍然需要更多的基于脑部的实验来论证,但不失为一种可能。而特曼提出的另一种说法也可能成立:负离子在接触皮肤的时候会中和皮肤上正离子的电性,如果正离子的确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那么负离子也的确成功抵消了正离子的效应,而实际上大脑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在富含离子的空气中呼吸有时也会用上鼻子,而人们认为鼻子也可以识别信息素,然后以某种方式向大脑传递积极的信息。

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
对生物机制的一些研究的发展预期也许可以解释空气离子。特曼曾经见过一个研究项目,医生给刚接受过负空气离子手术治疗的ICU肺部疾病患者测量实验数据,发现病人血液中,容易受情绪压力影响的乳酸含量在手术后急速下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一种因环境而产生低落情绪的病症)患者身上。特曼被这项研究所吸引,但仍然无法因此断定血液含氧量的增加是离子发挥了作用。而另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实验希望了解负离子环境中,季节性情感障碍患者的血液含氧量是否会有明显上升。如果有,那么研究人员可以继续深入,搞明白负离子是如何帮助血液溶解氧,以及为什么这会让人的感觉变得更好。
牛津大学的凯瑟琳·哈默最近也在进行一个关于离子如何影响情绪的严谨双盲实验(科学家和实验者都不知道哪些实验者接受哪一处理的实验技术)。对于特曼的研究,她说:“我们看过很多已出版的研究,都支持负离子可被用于季节性情感障碍的治疗,而这充满了阴谋论的色彩。没有人知道这些治疗是基于什么原理展开的。”
她开始参照Zoloft或者Abilify所做的实验,并以相似的实验条件来探究:离子是否真的会产生与他们的实验结果相同的心理变化。她说:“当人们感到沮丧时,人们会倾向于关注和记忆更多的消极事物而非积极的。”而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第一个心理环节。
在2012年的一个试验中,哈默聚集了一些季节性情感障碍的患者,并给了他们一套标准化的情绪处理方式测试,比如让患者辨认积极和消极的面部表情,回忆并列举积极或者消极的人格特征。季节性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倾向于辨认和记忆消极的事物,而同一实验中的健康人群并没有这样的倾向。
当哈默给患者实施了一套高浓度的负离子治疗之后重复测试,患者似乎在情绪处理方式方面有很大改善——比如辨别和回忆快乐表情和词语的能力有所增强。但这不止发生在患者身上。绝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参照组也是如此。
特曼与哈默二人对于实验室外的风暴对人所产生的情绪效应,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以免片面。而我们也无法测量世界上的天气现象与瀑布中已知的负离子微粒的密度,这一切都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存在动态变化。即便是这样,科学家们依旧希望对此进行推测。哈默说:“当然,像在临近瀑布的地方进行攀登,你也有可能受到由大自然产生的大量负离子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并没有用我们在实验室所做的方式来对此进行验证,所以一切都是未知的。”而她也提醒道,一些离子浓度的小范围变化也有可能导致人体身心双方面的变化。
看着实验室外的世界,特曼提到了他一位同事的工作。爱达荷大学的菲利普·米德最近发现,普通的淋浴房里的空气所含有的离子浓度竟然与特曼的工业离子发生器(比世面上出售的发生器有更高的功率)相当。特曼说:“我并不清楚这是否能够解释人们喜欢享受长时间的淋浴过程,或者喜欢在洗澡时唱歌。但是我们可以借此推断那些曾经流行的研究文献所声称的:暴风雨和雨后放晴的天气也许真的有同样的效果。可以想象,如果你每天起床后会进行一个30分钟的淋浴,其效果可能和我在临床实验中所采取的抗抑郁治疗相当。”

特曼认为:“可以想象,如果你每天起床后会进行一个30分钟的淋浴,其效果可能和我在临床实验中所采取的抗抑郁治疗相当。”
当我在暴风雨过后醒来,尽管发现世界已经恢复了平静,却似乎依旧能听到那场喧嚣。也许,就像一次淋浴或者瀑布下面的野营,巨大的气候现象会改变空气中的离子浓度,天气真真切切在我的肌肤之下对我起到影响,改变了我的大脑或者血液,也许两者都有。就像在新月的夜晚躺在田地里,风暴让我觉得自己融为了宇宙的一部分——微小、脆弱,但是真切存在。
当我打开我家的大门,所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许多直立的大树和各种柱子不见了。索性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砸到我的车或者房子,但不久后我就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幸运。
后来我了解到,这场风暴属于飓风,风速达到了100英里每小时。气象学专家将其命名为“北美超级飓风(derecho)”。这场灾难造成了30亿美元的损失,切断了近420万人的能源供给。
我所在的村庄经历了两周的断电断水。红十字会带来了帐篷、晚餐和碳水化合物;一个警察长官站在一个用瓦斯动力的发电机旁控制仅有的能源供给,电线有一英里长;一个住在镇子附近的老妪被发现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于家中;一个男人在清扫垃圾的时候突发心脏衰竭而又无法及时送至医院抢救而死亡。
但事情不总是糟糕的,暴风雨毁灭性的暴击使得人们像受磁性吸引的铁屑一样聚拢起来。在格林班克,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正在缓慢变质的食物,彼此帮衬着处理倒插在院子中的树干,相互邀请着参加点燃垃圾而形成的篝火晚会。他们带给彼此成桶成桶的饮用水,骑着自行车去为邻居朝商店赊账买来冷藏的炖肉罐头,彼此分享自己的灾难故事。
尽管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电力恢复,我们也将重新投入了工作,回到了饱经磨难却充满光亮的家里,而我们曾经相互依偎彼此取暖。我们无法避免地重回孤立无援的常态。但就像一个射出的电子将会去寻找并依附上一个分子,人类也总能聚集起来。毕竟,未来仍有数不尽的灾难,而我们需要彼此携手共度。
来源/利维坦
文/Sarah Scoles
原文/nautil.us/issue/37/currents/the-strange-blissfulness-of-storms
南先森致力于牙齿保健、正颌整形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也不定期分享杂七杂八,希望大家牙齿健康、颜值在线、忠于内心、疏于表演。如果凑巧你也是个有趣的人,那就扫码关注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