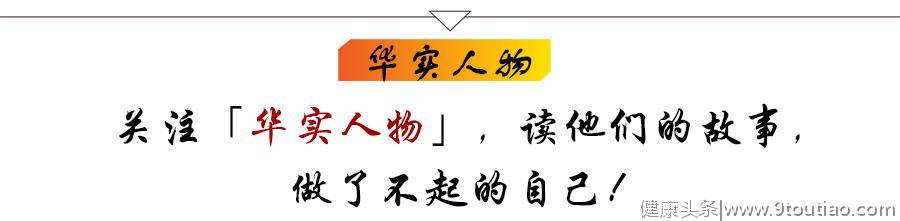捍卫活着,她在神经病院抗抑郁的38天



子曰:“不知生,安知死。”
此言差矣。对于左灯,大约是“不知死,安知生”的......
左灯的遗书写得很文艺:
“太孤独了!抑郁症的痛苦真的是一种孤独到极致的痛苦。
这种一个人苦苦挣扎的无助感,已经把我鞭笞得体无完肤......”
相形于那些“啊呀啊唷,我要死了”的矫情文字,这份遗书真情中确是透着斐然文采的。
左灯也这么认为,可她还是把这篇杰作揉撕成团,冲进马桶,并且恶狠狠地追唾: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让我去死?不存在的!”

话要从2017年冬,精神病区的大门在她身后砰然关闭时说起。
26岁的左灯有些后悔,像大多数人一样,在患病之前,谈及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名人,她既惊讶也无法理解:
“太消极了!”“世界这么美好,怎么舍得死呢?”“开心点不好吗?”
而现在她只好承认自己是乌鸦嘴,感叹“天道好轮回”。

再看眼前,仿佛正置身于平行宇宙的另一个世界,不知是科幻还是魔幻:
幽暗的走廊上,一些好奇怪的人正在僵硬地移动,或自言自语,或哭哭笑笑,
有的光着脚丫,有的满脸菩提,还有的向她亲切打起招呼:“哎?小花?你好呀!”
......

尽管这个世界有些诡异,但左灯却慢慢高兴起来,因为她越来越确认自己是这里的颜值担当。
“姐姐你好漂亮啊!”
左灯管那个嘴上涂了蜜的男孩儿叫弟弟。
“打牌吗?”那天弟弟从兜里摸摸索索掏出一副扑克,
也许是抗抑郁药开始发挥疗效,左灯胸中涌起一丝久违的兴致,于是三人噼里啪啦玩起了斗地主。
哦,是三人,第三个是位躁狂症阿姨,因为“躁狂”,所以喋喋不休,不休于门外世界满屏的心灵鸡汤,灌弟弟;不休于“伟大梦想你想实现吗”,问弟弟。
弟弟回:“活着”,然后突然一声惊叫,扑通倒地......
事后,连护士都心有余悸——“他让我们都觉得害怕”。
疯狂抽搐、大声嗥叫、掀床、袭医、镇静剂、束缚带......还有弟弟回答“活着”时的眼神,
这些情景不断在左灯的脑海里闪回:
活着,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却是我们拼死捍卫的梦想。
她想。

左灯的画

“你是什么病啊?”“你是怎么自杀的啊?”
“不要割腕,会有疤,你看。”“我吞了一整盒药呢!”......
在病区,不论此类骇人听闻却轻描淡写的聊天如何发端,都会以“活着啊老铁”的相互鼓励而结束。
因为即便在这个世界里,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悍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病友们各具特色的怪异举止和自杀行为只是生病大脑导演的恶作剧。
而相较普通人的误解,左灯觉得病友们彼此的“懂”,真是有亲人般的温暖。
这不,她就兴高采烈得给远道而来探望自己的闺蜜们介绍开了:
“这是弟弟、这是妹妹、那是阿姨......”

可看她这样,一位闺蜜却皱起了眉头:
“你没发现吗?你跟他们走得太近了。”
左灯沉默。
“你总要重新融入社会吧,你看你给你父母带来多大负担啊!”
几乎与此同时,左灯的眼泪就开始啪啪垂落了,落在跪于床上的大腿上,而大腿的颤抖说明她已哽咽,
至于闺蜜们脸部倏然的惊恐,则证明了当时她的尖叫飙到了“High C”。

没错,左灯发病了。
这不是脆弱,这就是“重度抑郁症”。
[其实,患上抑郁症,人多是想努力而无法努力,想坚强而坚强不起来的,
本身就会陷在自己糟糕状态给周围人带来麻烦的自责中,
所以,即便是出于善意,诸如“坚强”、“加油”、“努力”、“振作起来”、“别泄气”,
甚至“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类鸡汤话绝对不能对他们说,更何况所谓“恨铁不成钢”的尖刻言语,这只会增加他们的痛苦。]

我们从生到死,身心一体,好好坏坏伴随一生,其间情绪的波动在所难免。
但半年前,左灯本应正常波动的情绪,开始没来由地走向持续的悲观(注意,是持续):
捧着爆米花看电影,她觉得是在端着贡品上坟;
插上耳机听音乐,她觉得每首曲子都在奏响哀乐;
至于那本百读不厌的《傲慢与偏见》,也慢慢蒙上尘灰,任由达西和伊丽莎白在里面老去。
进而身体机能出现异常。
头痛、胸闷、身体被掏空的疲惫感自不必说,随时想不起手机放哪儿,碰翻水杯也成了家常便饭。
更有甚者,作为记者,本来伶牙俐齿的她,采访时居然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同事背后议论,“她是不是打了胎”。

然后,就在突然之间,她感到脑子里的最后一根神经“啪啦”一下崩断了,
下一秒眼前的一切事情顿然失去意义,“我这一辈子一定过不好了!”
左灯开始哭了,眼泪涌出眼眶,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
流到了脖子里,流到了胸口上。她抬起手去擦了擦,眼泪又流到了她的手上,
在她的手掌上流,在她的手背上流,
在她拧开的药瓶盖子上流,在她送进嘴里的一把又把药片里流......

(左灯自杀未遂,被老爸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我们发现那种持续而强烈的负向思维带给左灯的悲观与消极,已经无需理由的支撑了。
而抑郁症对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阴鸷地剥夺人对自我的控制权,
所以夺回自我,不仅是一场生死之战,也是一场尊严之战。

自从那次飙“High C”,左灯在病区算是“一鸣惊人”了。
“太丢脸了!”恢复精神后,她依偎着妈妈说:“哎呀,我都不好意思出病房啦。”
左灯也没想的,当自己真正摘下面具时,居然能这么轻松。
很多年来,她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人设”:
积极阳光的乐天派,调动气氛的“造high人”,还有温柔耐心的倾听者。
尽管她明知一个人不可能令所有人喜欢,但却接受不了任何一个人对她“不喜欢”,
所以宁可带着虚伪的面具做个“滥好人”。
而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人和小孩之间是平等,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随波逐流和特立独行也是平等的”。
总之,平等让左灯接受了人类必然的不完美。

不知不觉中,左灯的病也开始好转了。
比如:透过病房封闭的窗子,她开始看到远方缓缓驶过的火车,火车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彩色的”;
比如:她开始感到饥肠辘辘,恨不得吞下整个世界;
比如:她开始恢复古灵精怪的本性。出院的病友说想她,她就整蛊地问人家:
“你能不能在你妈面前,把头埋进马桶里狂喝水,再来陪陪我?”
再比如:她恋爱了!
你没看错,对于那位叫“易”的英俊律师来说,他必须要回答左灯提出的这个问题:
“你能同时拥有一个抑郁症的老妈和抑郁症的女友吗?”
易的母亲也患有抑郁症,他来医院陪床时遇到了左灯。
那天不知是由于抗抑郁药的副作用,还是突然脑洞大开的觉悟,
平时几乎不吸烟的左灯,居然问易:
“帅哥,有烟吗?”

于是,接下来在病区晾衣室卫生间的小隔断里,便出现了这么一幕场景:
一位穿着病号服的短发姑娘和一位表情尴尬的小伙子,大眼瞪小眼,挤在一起吞云吐雾,反而有点青涩的美好......
(要让医生护士发现了,准会杀了他们。)
至于那个现实的问题,易后来的回答很简单:“不在于我拥有什么,而在于我已拥有。”
左灯好开心,“你看!”她拉着易的手,指向窗外,“春光,在带露的繁华上开放了呢。”

春天来了,左灯终于可以踏出封闭了她38天的病区大门,她出院了。
当父亲的车开出医院的瞬间,恍若隔世的感觉扑面而来,她默默许愿:
“不要再复发了,让我活着吧!”

回到宁波市区的出租屋中,父亲给她退租收拾东西回老家,
正要拿起床头柜上的两张白纸时,左灯迅速跑到父亲面前夺下,然后揉撕成团,冲入马桶。
这篇遗书中的精品,倒究没有被用来承接亲人们的眼泪。哎,怎么说呢——谢天谢地!
易对她照旧体贴入微,父母对她更加宠爱有加,
远方的闺蜜也给她寄来抱枕,尽管上面印着闺蜜傻呵呵的大头照有些诡异。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活着多么好,能够思想多么好,好得左灯都不想睡觉......但她还是抱着睡枕睡着了。
觉醒了,闺蜜如约而至,父母、左灯,还有闺蜜几人欢聚一堂,开始在饭桌上和皮皮虾们“搏斗”。
“突然,汹涌而来的悲伤,像沾染毒液的藤蔓,一点一点往我身上攀爬......”
左灯又发病了,她在饭桌上哽咽,她在沙发嚎啕,她在妈妈怀里颤抖。
那天,左灯用了十五分钟才赶走抑郁症这只黑狗,然后他破涕为笑,发现由于哭得太突然,嘴里的饭还没有咽下去。
这就是抑郁症,精心的治疗在不断弱小它的力量,但它还是会顽强地挣扎,因为对宿主的控制是那么令它着迷。

现在,左灯的发病次数越来越少,终至于无,她到医院复诊,看着那些来来去去同病相怜的病友,她突然想:
“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朋友?大家知道他们的病吗?他们在孤独地抗争吗?”
如果世界洞悉了抑郁症的真相,他们会不会昂起头站在阳光里,告诉世人:
我生病了,但我在努力地活着!

左灯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将自己生病的经历和在精神病院的见闻记录下来。
在书中,她写道:
“人们经历的痛苦和它带来的意义,原来是有时差的,
有时需要耐心地等一等,答案才能被慢慢揭晓。”
是的,等一等。
也许我们正痛苦于生命的艰辛,但迟早有一天,我们会为它的美丽而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