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养生思想:道医大师传秘方,备急千年救世人
葛洪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各种炼养方术,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养生方法,不偏不执,要懂得气法、导引、房中、饵药、金丹,才能延年益寿,达到长生的境界。道教史上,葛洪以其卓越的成就,为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而享有崇高的声誉,受到了历代道教徒的尊敬。直到今天,我国一些道教名山如广东的罗浮山、杭州的葛岭、抱朴道院等还保留纪念他的建筑物、碑刻及炼丹遗址。在世界上,葛洪的名字早己载入古代科学家的史册,得到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著名科学史家斯蒂芬·F·梅森博士等人的高度评价。

葛洪(资料图)
葛洪的中医药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为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提供研究灵感,帮助她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为解决治疗预防疟疾这一世界医学难题作出贡献。屠呦呦也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而使道教医学的实践与成果,得以光大发扬辉煌世界。
葛洪学识渊博,精通医理药理,并长期从事炼丹内修的研讨,是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养生学家。我国传统的医药学和养生学本来密不可分,在当时医疗技术较原始又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养生对保障人体健康显得尤其重要。在长期医疗、养生实践的基础上,葛洪提出了自己的养生思想。
众术合修的养生体系
他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因而,他广觅道经,博览众术,对秦汉以来的各家各派养生内炼术都加以研究,认为各种方术都有不同的健身价值和养生功能,主张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出于这种认识,葛洪将气法、导引、房中、服食、养生、符咒、药饵、外丹等各类方法融汇贯通,汇于一体,形成了一个以气为本、众术合修的养生体系。
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首先阐述了他的元气说,为其养生学说建立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宇宙的本原是物质的元气,由元气的分化,才产生天地万物。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由气所生成的。

乾坤图 明代 绢本设色(北京白云观藏)
这种气生万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既是对秦汉元气说的继承,也是他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实验和探讨的结果。他在论自然变化的原理时说:“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认识到云雨霜雪都是天地之气变成的,天地之气就是一种自然的物质。扩而言之,自然界的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由气变化生成的。
这个气也是构成人体和生命存在的基础物质。他说“善行气者,内以养生,外以却恶。”强调了气与人体生命间的至要关系。同时又指出:“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叶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又说:“气绝之日,为身丧之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生命终止的内在原因。
对于人体致病夭折的现象,葛洪辩证地探讨了它的内因和外因。他说:“夫之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在他看来,引起疾病夭折的根本原因是体内气血的亏竭。他说,受气本多则伤损薄,受气本少则伤深。

丹台春晓图 文伯仁 明代 纸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用力役体,汲汲短法者,气损之候也。面无光色,皮肤枯腊,唇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减之证也。二证既衰于外,则灵根亦凋于中矣。”所谓“二证”即是疾病症状的显现,它是体内气血亏耗的必然结果。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现象,“以觉病之日,始作为疾”,而怨风冷暑湿等外界的因素。
对此,葛洪明确地指出:“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也,徒患体虚气少者,不能堪之,故为所中耳。”他举例说:“设有数人,年纪老壮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并冒严寒之夜……则其中将有独中冷者,而不必尽病也。非冷气之有偏,盖人体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独以给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钧器齐饮,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势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独以喝死者,非天热之有公私也。齐服一药,而或昏暝烦闷者,非毒烈之有爱憎也。”可见,内在因素往往比外界因素更为重要。
基于这种正确的认识,葛洪十分强调预防的重要性,主张把疾病消灭在隐患之中。他说:“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即逝之后。”“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以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着,则几乎知道矣。”

治身养性,务谨其细。(资料图)
他认为,日常生活中伤生的因素很多,如困思、强举,悲忧,极乐,汲汲所欲,寝息失时,房中无节,饮食过度等等,皆足以致伤损寿。主张起居有章,保持情绪精神的稳定状况,即“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葛洪的养生学说非常重视人为的作用,鲜明地表现了对天命观的否定态度。他说:“有仙命者,要自当与之相之夜。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也就是说,既使“仙命”的禀赋者,还是要经过一番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其正果,何况凡人?
在《至理》中,葛洪甚至把“命有自然”看作是愚夫的见解。指出延年益命的路径在于养生:“今导引行气,还精神脑,食饮有度,兴居有节,将服药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带佩符印,伤生之徒,一切远之,如此则通。可以免此六害。”所谓“六害”,指诸欲所损、老病所害、毒恶所中、邪气所伤、风冷所犯,为能致人死亡之害。六害不除,死亡且不免,焉能修仙长生?故葛洪主张,人要修仙,先学养生,免此六害,身体无病,才能进一步修长生不老的仙道。

“我命在我不在天”(资料图)
对人为的肯定,必然导致对天命的否定。他说:“大寿之事,果不在天地,仙与不仙,绝非所值也。”“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同时,又宣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这一中国养生史上震聋发聩的响亮口号,体现了何等宏大的气概和积极有为的态度。
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
葛洪指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叶,与众木则别。龟鹤体貌,与众虫则殊。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众木不能法松柏,诸虫不能学龟鹤,是以短折。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则可与之同功矣。”
尤其可贵的是,葛洪清楚地看到了巫医迷信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他多次批判了那些妄言祸祟,专以问卜祭祷为业的巫祝,嘲笑了不精医术、不务药石的庸医,指出祈祷鬼神是毫无作用。
他说:“若乃精灵困于烦拢,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劳逸过度,而碎首以请命,变起膏肓,而祭祷以求痊;当风卧湿,而谢罪于灵祗;饮食失节,而委祸于鬼魅,蕞尔之体,自贻兹患,天地神明,曷能济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补焉?夫福非足恭所请也,祸非重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祷延,疾可以丰祀除,则富姓可以必长生,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这种不信巫祝、不重祈祷的态度是正确的。

葛洪移居图 王蒙 元代 纸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根据内修外养的养生思想,葛洪提出了养生的基本原则,在于不伤不损。他说:“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又说:“禁忌之急,在不伤不损而已。”对此,葛洪列举了十三项伤损之事,其中有: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力所不胜,而强举之;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谈言笑;寝息失时;挽弓引弯;沉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欢呼哭泣;阴阳不交。他认为这类损伤之事积累多了会使人早死,“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
接着,葛洪又列举了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沭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卧露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

“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资料图)
除了以上饮食起居的养生事项外,葛洪还特别强调精神的保养。他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遗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攘祸而祸去矣。”
汤用彤先生曾云:“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以上十项,当即《养生要集》内容之大要,由此并可窥得当时道教养生学说之梗概。”(《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整个道教养生学的大致面貌,确如以上所论。葛洪以长生成仙为目的而研习仙方术,特别是他的金丹术、医药学、气功和养生理论,为道教和中国科技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把养生学纳入古代科学宝库之中。
内修外养的性命法诀
葛洪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各种炼养方术,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养生方法,不偏不执,要懂得气法、导引、房中、饵药、金丹,才能延年益寿,达到长生的境界。葛洪虽以金丹为大道之重,但实际上仍以气法的修炼作为延年长生的基本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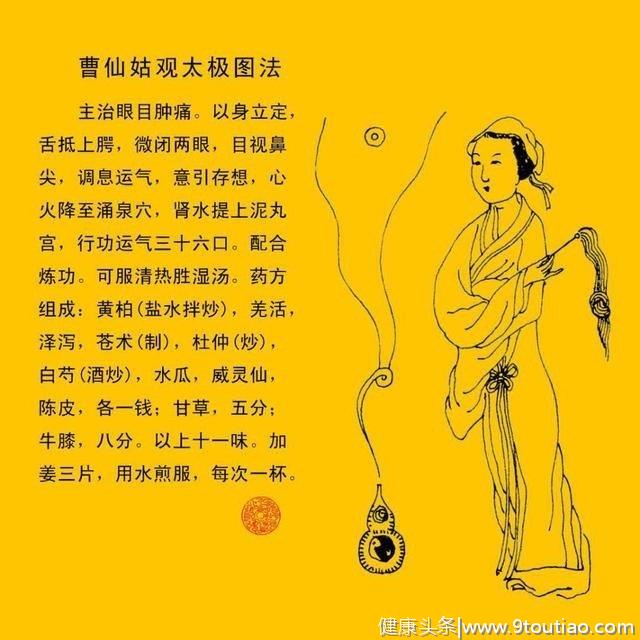
气法修炼以精气神为三宝,主张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葛洪已紧紧抓住精、气、神这三大要素进行修炼。葛洪说:“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便是修炼精、气、神的入手法门。
因为人不能恬愉澹泊,则识神用事,于是好恶心生,是非心生,名利心生,色欲心生,乃至神智昏乱,气息不定,精气流溢,后天之精、气、神动摇,伤及先天,人便会衰损速死。所以气功修炼之要,首先在于静定,人能恬静无欲,则识神退位,元神自生,于是心降而神凝,神凝则气聚,气聚则精生。
关于气法的校验,葛洪加以了全面的总结。他说:“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

“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气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应该承认,葛洪的这些记载许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其中一些例证已为现代气功师所证实。
那时道士已可用“以意领气”的行气法治病,“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除行气为自己疗病之外,还能以气与人祛病,这在当时谓之“布气”。《晋书·艺术列传·幸灵传》载:“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余年,灵疗之,去皇氏数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顷,顾谓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仓卒起邪?灵曰:但试扶起。于是两人夹扶以立,少选,灵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

炼丹图 黄慎 清代 纸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道士幸灵用布气的方法给人治愈痿痹病的例子,描述得活灵活现。葛洪说:“虽云行气,而行气有数法焉”。“故行气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治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
当然,在众多的炼养方术中,葛洪最重视的是金丹(外丹)。他认为,延长人的寿命,主要依靠内修与外养两个方面。所谓“内修”,如上举的气法、导引之类。所谓“外养”,即指服食、金丹之类,而又以金丹最要紧者。他在《金丹》和《黄白》两篇中,具体地介绍了许多炼丹的方法,其详密程度是葛洪以前任何道书里没有的。
他所记载的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和大量的炼丹药物,对研究汉晋时期炼丹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以《金丹》篇为例,它涉及的药物有铜青、丹砂、水银、雄黄、矾石、戎盐、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赤盐、曾青、慈石、雌黄、石硫黄、太乙余粮、黄铜、珊瑚、云母、铅丹、丹阳铜、淳苦酒等22种,这比《参同契》里提到的药物要多得多。可以说,是他奠定后世外丹术的基础,从而为南北朝隋唐时期道教外丹术的盛行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