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临终关怀病房见证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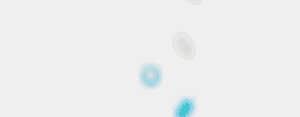
快言快语的东北女性刘寅,一点也看不出快六十的样子。去年她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筹建了安宁疗护病房,病房门口用中英文写着临终关怀倡导者西西里·桑德斯的一段话:“你很重要,因为你是你,即使活到最后一刻,你仍是那么重要⋯⋯”
做了一辈子肿瘤科医生,刘寅见证了太多病人的离世。随着安宁疗护理念的推广,一些病人在身体“没有积极治疗价值”之后,接受着人生最后阶段的姑息治疗。刘寅说,做安宁疗护的人,需要识别他人的灵性痛苦。这项工作也可以做到和助产士一样,一个是帮人喜悦地迎来生命的奇迹,一个是帮人平静地接受生命的消失。而一个人死亡时能否平静,牵涉到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现实。
口述|刘寅
采写|吴琪
摄影|黄宇
患者何时不再需要积极治疗?
我曾经是北京一家二级医院(后晋级为三级医院)的肿瘤科负责人。医院在北五环外,我们的病人既有北京本地人,也有来京务工人员,还有这些年通过努力在北京安了家的一些人,他们的父母病了后被接到北京治疗。二级医院很难获得首诊的肿瘤病人,到我们医院治疗的,一般都是之前辗转过好几家三级医院的中晚期癌症患者。我能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疲惫和纠结,比如癌痛、经济压力、离世前的悲伤,很多病人在躯体和精神上忍受着非常大的痛苦。
十几年前接触到姑息治疗理念时,我非常感兴趣,在医术之外,我对病人的处境特别能够产生共鸣。当时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刘端祺主任作为北京抗癌协会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积极推广姑息治疗的理念,得到学会里同仁们的积极响应,我也受到了这些理念的感染,开始了对临终关怀的深入了解和实践。2012年我所在的二级医院成为了卫生部首批67家“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这让我对通过控制癌痛让病人感到舒适,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
退休后,我到了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在肿瘤科建立了安宁疗护病房。目前我们做安宁疗护的对象基本是肿瘤病人,因为晚期肿瘤病人的生存期相对容易评估一些。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一般都与肿瘤科在一起。我们的安宁疗护病区有静修室,有病人画的画儿,有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温暖的话语。接触的病人多了,我发现安宁疗护工作与一个国家的死亡观念、历史文化、患者个人经历等密不可分,有着浓厚的本土特色。一个在医学上“没有治疗价值”的病人,还要不要用抗生素?要不要输血?这些涉及医疗原则、伦理,更涉及病人和家属的诉求,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而不能把安宁疗护的理念和原则绝对化。
从定义上来说,通过医学治疗无法解决这个病人的疾病问题了,才进入姑息对症治疗。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是非常忌讳谈论死亡的,一个病人选择什么态度面对治疗,很多时候没有经过与家人、与医生充分有效的沟通,病人因为对疾病了解的局限性,对治疗方案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他们最后的决定不成熟。什么样的病人应该进入姑息治疗阶段,需要面对每个具体的病人来做判断。从生存期的角度看,一般是在生命的最后3〜6个月。

刘寅在与病人和家属聊天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病房来了一个患肺癌的老人。老人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学教授,快80岁了,一儿一女分别在国外和北京工作,我叫他张老师。初诊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小细胞肺癌(广泛期)、上腔静脉压迫(颜面及四肢水肿)、两侧胸腔积液、肝转移、骨转移,整个人憋喘很严重。我查房时,张老师非常不情愿地在吃之前医生给他开的依托泊苷胶囊(VP16),他坚决拒绝系统治疗。他为什么不接受治疗?我与病人和家属聊下来,获得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张老师的夫人死于食管癌。夫人做了放疗和化疗,受了好多的罪。等到张老师自己得了癌症,他想起化疗就有心理阴影。他的说法是:“让我早点结束,别让我受罪就行。”第二,张老师查出癌症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他觉得自己不久就要离世了,对自己病情的判断非常悲观。
小细胞肺癌的初次化疗效果一般会非常好,在我看来,张老师当时放弃治疗太可惜了。我第一次动员他时说:“我们给你把胸水(胸腔积液)放一放,胸腔里打点顺铂(一种含铂的抗癌药物),行不行?”他不同意。
过了一个星期,他吃VP16胶囊确实没什么起色,我又跟他沟通。“你这个小细胞肺癌现在处于第一次治疗阶段,不治有点可惜。你喘憋这么重也不舒服,我以改善症状为目的来给你治,咱不以治疗肿瘤为目的,你说好不好?”接着我又说,“张老师,我们用药的目的呢,主要是让你的身体感觉舒服。而且你看2020年的春天,这个世界太热闹了,咱们争取一起看个完整的春天,好不好?”
我沟通了两次,这位老教授同意了。考虑到患者的年龄,我用了正常治疗量三分之二的药量,尽量减少药物的副作用,让病人身体不难受。三天后病人水肿基本消失,第二周期我们给他用了VP16口服加静脉顺铂,他的上腔静脉压迫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胸水得到控制,人也不需要吸氧了,整个人舒服多了。
接着,张老师的孩子从美国回来了,他的情感得到进一步支持,再加上身体感受舒服了,对治疗变得积极了。家属和我商量后,我给张老师加用了新的免疫制剂。张老师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要是能再活两三年也挺好的。”我跟他说:“张老师,您记得我给你的承诺吗?我希望您的症状能够改善,活得舒服些,咱们争取看一个完整的春天,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共同努力活好每一天,好吗?”
到了8月,张老师的病情又反复了。他的女儿来与我交流,她说她很纠结,要不要给爸爸积极治疗。我跟她说,第一次我鼓励病人积极治疗,是因为一线治疗我有70%的把握,现在是二线治疗阶段,30%的把握都没有了,肿瘤在病人体内已经广泛性转移。广泛期的小细胞肺癌,总体生存期本就不超过半年,你爸爸已经过了5个月,很好了。他女儿不死心,带张老师去外院做了伽马刀,病人反应非常大。最后,他女儿下决心不给张老师做抗肿瘤治疗了。其实她已经与病人交流过,虽然病人心里充满渴望,但是理智上是能接受现实的,他已经需要进入姑息治疗阶段了。张老师对我说,你真的是让我好好活了一个春天。当然,是否接受治疗仍然以病人意愿为主,我是从医学角度给他提供建议。
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世
一个晚期的肿瘤病人,如果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病人有医保,家庭关系和睦,再加上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解,我们与他的沟通就会顺畅,医患关系也会简单。现在控制癌痛的手段比较成熟,只要人们观念到位,能够接受疼痛控制的治疗,解决躯体疼痛不是一个大问题。即使是这样,在医生层面,具体治疗癌症病人时,有些医生还是容易忽略控制疼痛的问题。我在我们科室也需要频繁地提醒年轻大夫:疼痛控制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安宁疗护工作是希望陪伴病人走好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随着这些年接触的病人越来越多,我感觉家庭和社会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病人能否安心离世。比如有经济纠纷的家庭,病人就很难平静。这些年城市化改造的过程中,很多城市家庭经历了拆迁,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对文化和习俗也有一定的影响,完全没有经济困扰的家庭其实并不多。还有进城务工的家庭,要花多大力气来治疗一个病人,与整个家庭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家庭成员对亲情的理解、需求各有不同。在病人的重大治疗决策上,我们科室有个家庭会议制度,让病人与能够做他代理人的亲人,来和我们医生一起讨论制定对患者更为有利的治疗决策。但有时候要做到这一点,也相当不容易。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同行的电话,说有一位著名学府的老教授,人快不行了,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麻烦我关注一下。急诊科跟我们联系,说这位老教授已经处于弥留状态。我跑到急诊科一看,一位衰弱的老人躺在那里,身下不断地有血便出来,看上去非常可怜。我问他:“您感觉怎么样?”老人家说:“我要安乐死。”这个显然不现实。我问他:“您家里人呢,谁能管您?”旁边站着一个保姆模样的人,她说老人的老伴已经去世,孩子们都在国外,她只给老人做了两三个月的保姆。我问:“能联系到谁?”保姆说:“老人有个学生叫张大宁(化名),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办理。”
我让保姆先给老人在国外的孩子打电话,急诊室里人来人往,沟通效果也不好。我对老人的孩子说:“急诊评估老人的生存期只有一周了,现在因为新冠疫情,你们马上回国也不现实,你得告诉我,你们授权谁来做治疗决策。”老人的孩子说,那只能是老人的学生张大宁。我们给张大宁打电话,他有事情赶不过来。我对急诊医生说:“只要有委托监护人签字,就可以收入院。”夜里值班医生又与老人的女儿沟通。这家人有一个特别大的分歧:老人坚决要求回家,不治疗,死在家里;孩子们都要求医院积极治疗。没有家人的授权,保姆不敢带老人回家。
老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于是根据电话里老人孩子们的坚决要求,医生给老人输液、止血,联系血库准备输血,又给老人插了胃管、导尿管,给他输氧。第二天早上我查房的时候老人清醒过来,老人说:“你们给我弄这些,我同意了吗?都是骗子,医院也是骗子。”后来我们了解到,老人一直不同意住院治疗,直到前几天出现血便,因坚持不来医院,处于休克状态了。保姆急急忙忙与他在国外的孩子们视频,老人睁眼看到了女儿的影像,以为女儿回来了,答应去医院。他认为即使去到医院,也只是接受一点支持治疗。等老人在我们科室清醒过来,发现女儿没回来,自己还被迫插管,感到非常气愤。
我们的社工志愿者一直在配合我们医护人员做临终病人的安宁疗护。志愿者佳奇尝试与老人聊天,老人态度很冷淡。等到佳奇要离开的时候,老人突然拽了一下他的手,把保姆支了出去,对佳奇说:事情很复杂,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我们这位社工很感动,后来提到好几次,老人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替别人着想。佳奇还是想给他提供支持,与他聊了几次。老人说,他有明确的嘱托,就是希望安安静静地死在家里,不要让他受折磨。他想把房子捐给自己所在的大学,但是这牵扯到家人利益,很难实现。老人几年前就为死亡做准备了,把银行卡都清理了。他说他这一辈子培养过很多人,成就过很多人,做过不少好事,但是轮到自己要去世了心愿却很难实现,他发现别人真帮不了自己。
老人一再要求回家安静离世,我赶紧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家庭会议,孩子们在国外怎么办呢?那只能线上开会。开会的时候,老人单位负责管理退休人员的工作人员、学生张大宁也来了,照顾过老人的三个保姆全来了。疫情期间真的是不容易。但遗憾的是,因为时差的原因,开会时老人的孩子们没有联系上。
因为没有直系家属在场,谁也不肯签字带老人回家。两天后老人去世。一直到老人去世之前,保姆还在骗他:“我们回家,我们马上回家。”我内心真的很难过,老人家就一个心愿——回家。为什么就是满足不了呢?!
最后的忏悔
今年6月的一天,一位北京老大爷被人送到我们病房,办完住院手续后,送他的人就走了,留老人孤身一人。这位贾大爷骨瘦如柴,送来之前5天没有吃饭了,前列腺癌已经全身骨转移,并且骨转移导致左侧上下肢骨折卧床不起。他显得邋遢,一看就是没人照顾的。但老人家头脑很清醒,虽然整个人是一副很不合作的样子。我问他:“你家谁替你作主,我们该联系谁?”一看他的手机通讯录,十几个电话,只有两个是有名字的:一个是我们医院前段时间照顾过他的护工,一个是上次送他入院的女孩,这次送老人来住院的是房东。贾大爷说他在出租房的7万多元存款刚刚被偷了,身上没钱。
我们又问老人到底有没有家人,他说有儿子,平时不来往。他告诉我们他儿子的姓名、电话,可是我们给这个儿子打电话,一说他爸爸的事情,他马上就挂断电话,再打就不接了。我们评估了一下,贾大爷的生存期只有三周了,我们找不到人管他,可是也不能把他放到大街上,那太不人道。我们向医院汇报,经院里同意后我们报了警,警察说他儿子的信息属实,其他的事情警察也管不了,让我们找民政部门。我给科室医护们开会时说,这样的老人,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他儿子不接电话,没有微信,我让护士长天天给他发彩信,把贾大爷的医治情况发给他看,虽然从来收不到回音。我们还咨询了律师,志愿者佳奇打了好几个电话给老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街道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拆迁,空挂户口的人员很多,疫情期间查起来也不方便。护士长自己掏腰包给他买吃的。贾大爷还挺挑剔,这个米糊还行,那个馄饨不好吃,说草莓还可以。
贾大爷住院的第12天,他跟我说,他要死了,活不过当天。我知道他惦记儿子,问他:“我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你儿子发短信?”发完他想说的,我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想见你爸爸最后一面,请你尽快过来。”我们不知道他儿子会不会回话,等待的过程有些熬人。我出门诊去了,等到中午回到病房,护士长特别高兴地说,贾大爷的儿媳妇下了班就过来。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我告诉贾大爷的时候,他的神情马上就不一样了,像换了个人。
等儿媳妇到来后,她给我们讲了13年前老爷子与老伴离婚,拿走家里全部现金并断绝了父子关系,之后再无往来。我对贾大爷的儿媳妇说:“老爷子非常想念儿子和老伴,他说如果能见儿子一面,这辈子就可以翻篇啦。”贾大爷的儿媳妇说:“他们父子的矛盾太深,很难化解。我这几天天天和他说,他坚决不来,还对我发脾气。”
我跟贾大爷的儿媳妇沟通,说我给出三个理由,希望儿子来看看他。第一个,不管他对他爸有多大怨恨,希望他在他爸活着的时候能把这怨气撒出来,而不是带一辈子;第二个,我不希望等他到晚年,回想起今天的事情后悔,他应该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好榜样;第三个,如果老头还有什么财产方面的问题,不管他是有钱还是负债,希望他在活的时候跟你们讲清楚,这样处理起来要方便得多。
本来这些事情都是病人的家务事,我们医护人员参与深了并不合适,可是如果不把贾大爷的心结解开,贾大爷是不会走得心安的。安宁疗护中有太多的事情不是靠医疗手段能够解决的。安宁疗护所提倡的“全人、全家、全程、全队”四全照顾,也体现医学是有温度的人文关怀,是安宁疗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宁疗护病区很注重病人的精神需求
等到第二天中午11点多,贾大爷的儿子来了!他是一个50多岁的憨厚中年人。他冲我作了一个揖,我还了礼。我叫他贾师傅。贾师傅说:“老头的罪孽三天说不完。”我说:“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你能过来我真的非常谢谢你。其他事情晚点说,我们先去看看老人。”贾师傅走到床前,拉着老爷子的手叫了一声“爸”。贾大爷模模糊糊中慢慢转过身来,睁眼看了一下,以为是做梦呢。贾大爷见到儿子,唉,本来很混不吝的一个老头儿,真的是戚戚哀哀地哭了五分钟,一手摸着自己的耳朵,一手捂着胸口,说不出话。我们赶紧给他舌头下塞了两颗速效救心丸,怕他太激动。
贾大爷一直在问儿子:“你妈知道你来看我了吗?”其实他老伴两个月前就去世了,儿子没有告诉他。
从病房出来,贾师傅跟我说,他的手机号早就应该换掉,之所以留了这十几年,“就等着最后一天,看是火葬场还是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收尸”。他也一直留着父亲离家时写给他的纸条——“生不赡养,死不送终”。贾师傅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主任和护士长,我今天是不会来的,我不来对不起你们。他生了我,我给他送终,这就是缘。您放心,后面的事我会负责的。”我跟他说,不要只是怨恨你爸,他年轻时遭遇了命运的不公,也是个悲剧人物。
贾师傅每天看我们发的信息,心情很复杂,也不相信现在还有医护人员会管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做安宁疗护的人也有成就感,并不完全只有悲伤和痛苦。做我们这个工作的人可遇不可求,一个人能不能识别他人的灵性痛苦,或许也是种天分。安宁疗护与心理健康、个人诚信、法律援助、殡葬服务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这个行业还有很多工作体系需要搭建。有时候我也跟同事讲,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医生护士该做的,但是安宁疗护把我们的职责外延扩大了。

刘寅与她的团队
贾师傅探访后,又过了11天,贾大爷去世了。去世前那几天我们跟他聊天,问他有什么心愿,希望穿什么样的衣服离开,他回答说“随便了,无所谓了”。儿子来过,他的心愿已了,满足了!他跟儿子见面时也提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妈,她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对于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来说,临终前他忏悔了,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也算不容易。
贾大爷去世后,贾师傅把父亲的骨灰葬在了他爷爷的身边,并说服了亲戚们,同意他爸爸与他妈妈合葬。这对贾大爷来说,也是个圆满结局了。
既然死亡不可避免
前段时间,一个老人在和我聊到死亡时说:一个人去世,有三重意义上的消失:第一个是肉体上的消失;第二个是社会关系的消失,比如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社保这些的消失;第三个是记忆的消失。一个人说话的声音、笑声,会消失。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但希望子孙们不要太快忘记我。我觉得老人总结得太到位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谈话呢?因为老人家的两个儿子,不忍心与父亲做这样关于死亡的对话。两个儿子非常孝顺,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小儿子为了照顾患癌的妈妈,还辞去了工作。待到父亲查出癌症晚期,两个儿子心里很崩溃,觉得无法向父亲挑明,也觉得父亲承受不了癌症晚期的事实。
所以我承担了谈话的“任务”。我接触下来,觉得老人家非常开明。我们遇到不少家属,不告诉病人实情,一再说病人会崩溃,但是事实上,一个人面对死亡时,往往比家属预计的要坚强得多。
我把老人的话转达给他的两个儿子,建议他们把老人的照片做成视频合集,让他知道,记忆会保留。两个儿子孝顺,很不愿意谈论父亲即将离去的事。他们对老人照顾得很好,兄弟俩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可是尽职尽孝,每天都来看望父亲。
老人很豁达,他知道自己不久将离世,他是这样跟我们说的:“第一,希望我不是痛苦地走;第二,如果我走了,家里就没有负担了;第三,可以给国家节省资源。”一位80多岁老人的觉悟,让我感动。每个人对死亡的看法不同,但每个人最后的心愿,都打上了他成长的时代烙印。一个人年轻时受到的教育,影响他一辈子,死亡面前也是这样。
我们这里还有一对知识分子,也是80岁左右的老人。两人在新华社工作了很多年,早年是学小语种的大学生。丈夫到了癌症晚期,妻子总是让他坚强,老太太说:“你可是布尔什维克,你要坚强,老同事们来电话都让我转告你——要战胜疾病,要活着。”老先生说:“这样拖着太痛苦了,我不要坚强,饶了我吧,放我走吧。”按照我们的办法,我召集主管医生、护士和患者的老伴、女儿一块在床旁开了个家庭会议,病人表达了他希望尽快结束痛苦的愿望。我跟老人家说:“咱们不去主动结束生命,但也不去延缓它,这个过程我们尽量让你不感觉痛苦,行吗?”一家人很快达成一致,同意姑息治疗。
两天后就到了老先生弥留之际,他拉着老太太的手,说了一句外语。老太太后来告诉我,老头儿最后用西班牙语对她说“我爱你”。老太太一辈子都埋怨老头儿不浪漫,这最后的告白,是相当浪漫了。
那天家庭会议后,老两口关着门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老太太今后跟着上海的弟弟妹妹一起生活。老先生一去世,上海的亲人过来接老太太,她就跟着走了。这是对死亡和生活都看得非常通透的一对老人,我觉得他们是幸福的。
安宁疗护也叫临终关怀,是帮助人们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一种方法。安宁疗护人是伴行者,如何帮助人们“智慧到彼岸”,要求我们不断地探索和践行。做安宁疗护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怎么挣钱,还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情感,但我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和成就感,虽然很多人不理解。好的安宁疗护,能够使我们发挥类似助产士的作用,帮助病人安心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3期,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作者档案

吴琪
珍惜署名权,好好写字!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