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众疾之王,起于人亦止于人
李咏走了。有网友(@乔得克)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抗癌17个月,得癌的时间可能更久,这个过程一丝风声没有走漏,之前在美国被拍到,还被骂捞够就走……悄悄抗争,慢慢退去,渐渐被遗忘……这挺酷的,也挺让人难受的,李咏。”很快被数万次转发。
李咏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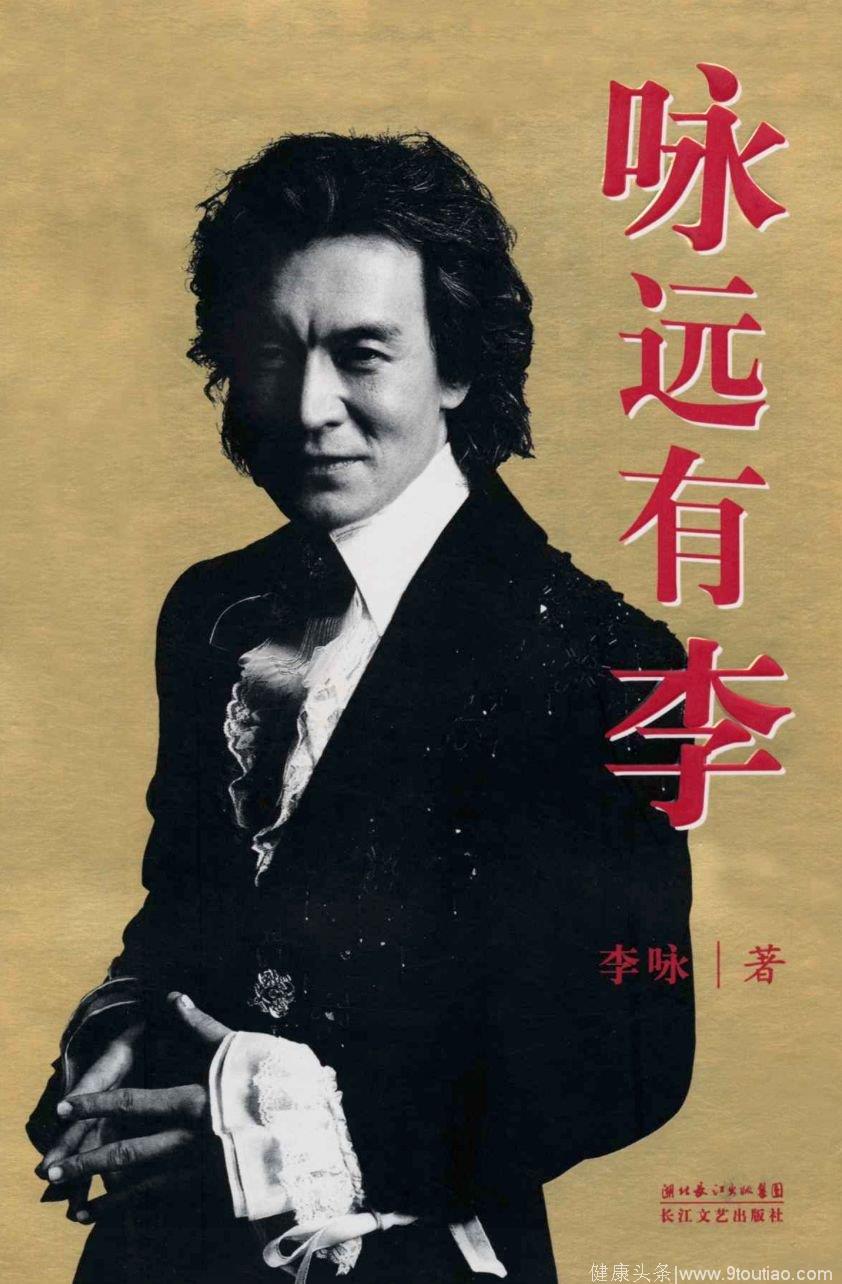
李咏(1968年5月3日-2018年10月25日)。图为李咏个人作品《咏远有李》(版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年11月)书封。
而同时,他的离开,就像以往所有引起关注的“患癌逝世”一样,也再度唤起我们对于癌症的恐惧。长期以来,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通过公众人物、新闻事件或身边的例子,来提醒自己生命的脆弱。
癌症,众疾之王。癌症起于人,亦止于人。
我发现,几乎所有寿命超出统计学预期之外的癌症患者都有着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是的,我也许会比预计的更早去世,但是我也有可能比预计的活得更久。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从现在起尽可能地好好活着。无论最后发生什么,这都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这句话出自一位叫大卫·塞尔旺-施莱伯(David Servan-Schreiber)的医生,他身为壁球队队长、医学博士、“身体非常健康”,在学术事业正走向巅峰的时候,被意外检测出核桃大小的脑部肿瘤。
他和朋友乔纳森·科恩,正在攻读博士,年纪轻轻就因为杰出的学术成绩,联合创办并一道管理着一个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建立的脑功能成像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目的是探索人类思维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从而了解人类思维的机制。然而,在那个普通却令人绝望的夜晚前,他从未想到这个研究会向他揭示的东西:他自己的绝症。那年他31岁。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1961年4月21日-2011年7月24日),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科临床教授,因其在精神病学所取得的成就,他赢得了2002年宾夕法尼亚州精神病学协会总统奖。他是“无国界医生”在美国分支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91年作为志愿者前往伊拉克。
从那之后,癌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位醉心于科学研究,对看护病人无甚兴趣的医学高材生,开始走近癌症患者,与他们一起审视生命和死亡恐惧。2011年,与癌症抗争18年后他走了,远远超过所谓的医学统计预期。期间,他每周骑一次自行车,常常打壁球,“带着癌症健康地生活”。
他将自己的抗癌经历,加以医学解读写成一本书《每个人的战争》(Anticancer: A New Way of Life),一度成为全球畅销书。在书中,他对医学的进步和局限,以及社会不平等都作出了自己的反思。如何直面、审视并克服恐惧,抗癌考验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限度。
原文作者 |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译者 | 张俊
摘编 | 西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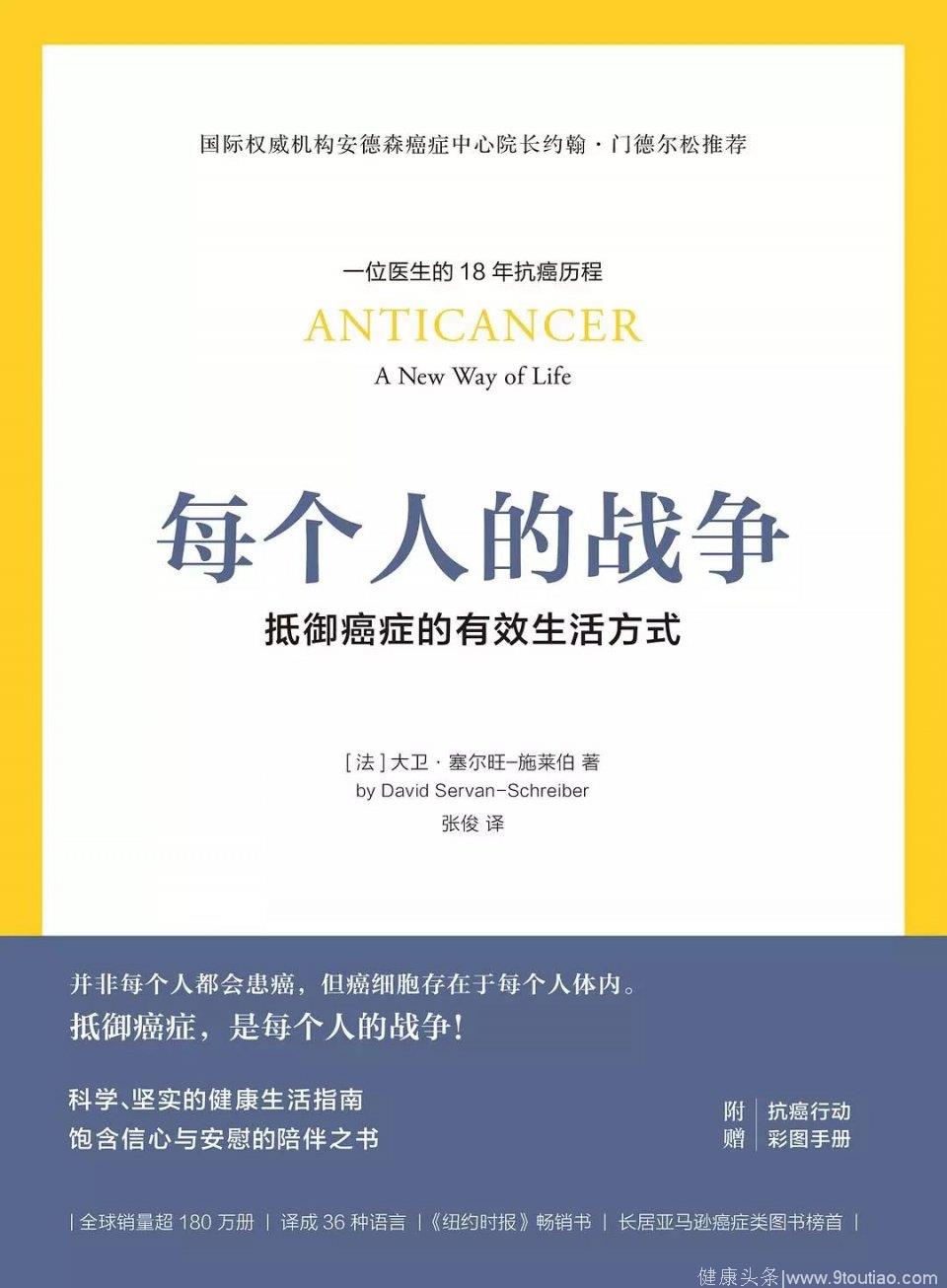
《每个人的战争》
作者: (法)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译者: 张俊
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大卫,你知道吗?这完全可能。”
在30岁及其以前,我从没有真正地对与病人的接触和沟通产生兴趣,而是忙于精神病学实习和实验室研究。我取消了(博士)培养计划所要求完成的轮岗任务:花6个月时间在普通医院看护那些因身体疾病而产生心理问题的病人(有的接受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有的做过肝脏移植手术,还有的身患癌症、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对阻碍我继续进行实验室研究的轮岗工作,我毫无从事的欲望。而且,这些病人都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想要做的是研究大脑、撰写论文、在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以及为科学的进步作贡献。毕竟,我还年轻,又野心勃勃。
 匹兹堡大学校园。大卫·塞尔旺-施莱伯是该校医学院精神科临床教授,也是整合医疗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图片©视觉中国
匹兹堡大学校园。大卫·塞尔旺-施莱伯是该校医学院精神科临床教授,也是整合医疗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图片©视觉中国
但是随后(指作者31岁之后,期间经历婚变、再恋爱——编注),我的生活却急转直下。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10月匹兹堡的那个迷人夜晚,秋色染红了街道两旁的树叶,我正骑着摩托车前往核磁共振检测中心,乔纳森、道格和我将会在那里与一些学生碰面,这些学生是我们某个实验阶段的“受试者”。我们会花钱让受试者钻进扫描仪,并让他们完成预先设计好的脑力测验。第一个学生8点钟过来了,按照计划,第二个学生的实验时间是9点到10点,但是他没来。
乔纳森和道格问我是否愿意上扫描仪。自然,我同意了。我躺进扫描仪的窄筒里,胳膊紧贴着身子,像躺在棺材里一样。很多人都受不了扫描仪那令人憋屈的空间:有10%到15%的病人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无法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检查。
就这样我进了扫描仪。10分钟后,解剖图像扫描完成了。在我眼睛的正上方有一个小屏幕,我等着从那里看到之前设计的用来激发脑前额叶皮层(这正是实验的研究对象)活动的脑力测验题。这个测验的内容是:屏幕上会快速不断地出现一组组按顺序排列的字母,每当你看到有一组字母与之前出现的完全相同时,就按一下电钮。我一直在等着乔纳森给我发送脑力测验题。
但是,扫描迟迟没有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乔纳森和道格就在屏蔽玻璃后的控制室里,我们只能通过对讲机交流。这时,我的耳机里传来了说话声:“大卫,我们遇到了点问题,图像上有个怪东西,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扫描。”好吧,我可以等。
我们又做了10分钟的解剖图像扫描,接下来就该开始脑力测验了。这时耳机里又传来了乔纳森的声音:“听着,情况不大对劲,我们要进来了。”他们走进扫描室,把我从扫描筒里拉了出来。我一出来便发现两人的神情有异,乔纳森一手扶着我的胳膊,说道:“实验不能进行下去了,你大脑里有东西。”于是,我让他们给我看看刚才扫描两次记录下来的脑部图像。
在我脑前额叶皮层的右部区域,有一个核桃大小的球状物体。在这个位置的肿瘤,既不是那种有时人们认为可用手术去除的良性脑肿瘤,也不是最恶性的脑肿瘤,比如脑膜瘤或脑下垂体的腺瘤。但是,我的身体非常健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我甚至还是壁球队的队长,因此,这不可能是什么囊肿或脓疮。
问题十分严重,晚期的脑部肿瘤要是不进行治疗,6周内就会要人命,即使采取治疗,患者也只能撑个一年半载。我不知道自己的肿瘤到了哪个阶段,但是我很清楚以上的数据。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在他的书房接受媒体采访。图片©纽约时报网nytimes.com
我骑上摩托回到城市另一头的小屋时,已是晚上11点,皓月当空,万里无云。卧室里,我躺在床上,睁眼望着天花板。这些年在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上,我一直苦心孤诣,蓄势待发,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我牺牲了很多,为未来打拼,突然间却发现,我可能再也没有未来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叶孤舟,原本在顺河漂流,突然间却被一个大浪托至岸边,掉进了一潭死水,再也到不了大海。造化弄人,我被困在一个了无牵挂的城市里,在匹兹堡独自一人,即将离开人世。
我并不想睡去,而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眼睛盯着印度小卷烟燃起的丝丝烟雾,这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我突然听到脑海里冒出一个声音,一个温和清晰,自信果敢,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确凿无疑的声音。这不是我,但这的确是我的声音。
当我反复念叨“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可能”的时候,这个声音说道:“大卫,你知道吗?这完全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既令人惊讶又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回答令我不再软弱无力。是的,这当然是可能的,这只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很多人都经历过,我并没有什么特别。
审视恐惧,它们并非不可抗拒

作者抗癌史 Anticancer: A New Way of Life 2008年封面。
在我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的那一周里,我疯狂地看医生,从这个预约冲到下一个预约。一天傍晚,天下着雨,我正在15楼的候诊室里等着医生。我站在平板玻璃窗前,向下俯瞰着街上如蚂蚁般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那些人是如此鲜活;他们有事可忙,有未来需要规划。至于我,死亡就是我的未来。我把视线从这群路人身上移开,感到一阵恐惧。
与出生一样,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是特例,那么我怕什么呢?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的病人教会了我如何去认识和掌控对死亡的恐惧。借助他们的经验,我开始懂得,对死亡的恐惧只是众多恐惧中的一种。而一旦审视这些恐惧,它们便不是那么不可抗拒。

《抗癌的我》(50/50 ,2011)剧照。
1
对痛苦和虚无的恐惧
我见到丹尼斯时,他只有32岁,却即将不久于人世。我们年纪差不多,而且像我一样,他也是一名医生。他已经被淋巴瘤折磨好几个月了,治疗也已经没有效果。
“首先帮助我的是一天早上我醒来时意识到,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死的人。虽然我会死得很早,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船上,路人、电视新闻主播、总统,甚至还有你。”他说这番话时没有看我,“你也会死,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想想这个我就很欣慰。这个我们共有的命运意味着我是一个完整的人,和你们大家、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后代紧紧相连。我没有丢掉我的人籍。”
延伸阅读:人类抗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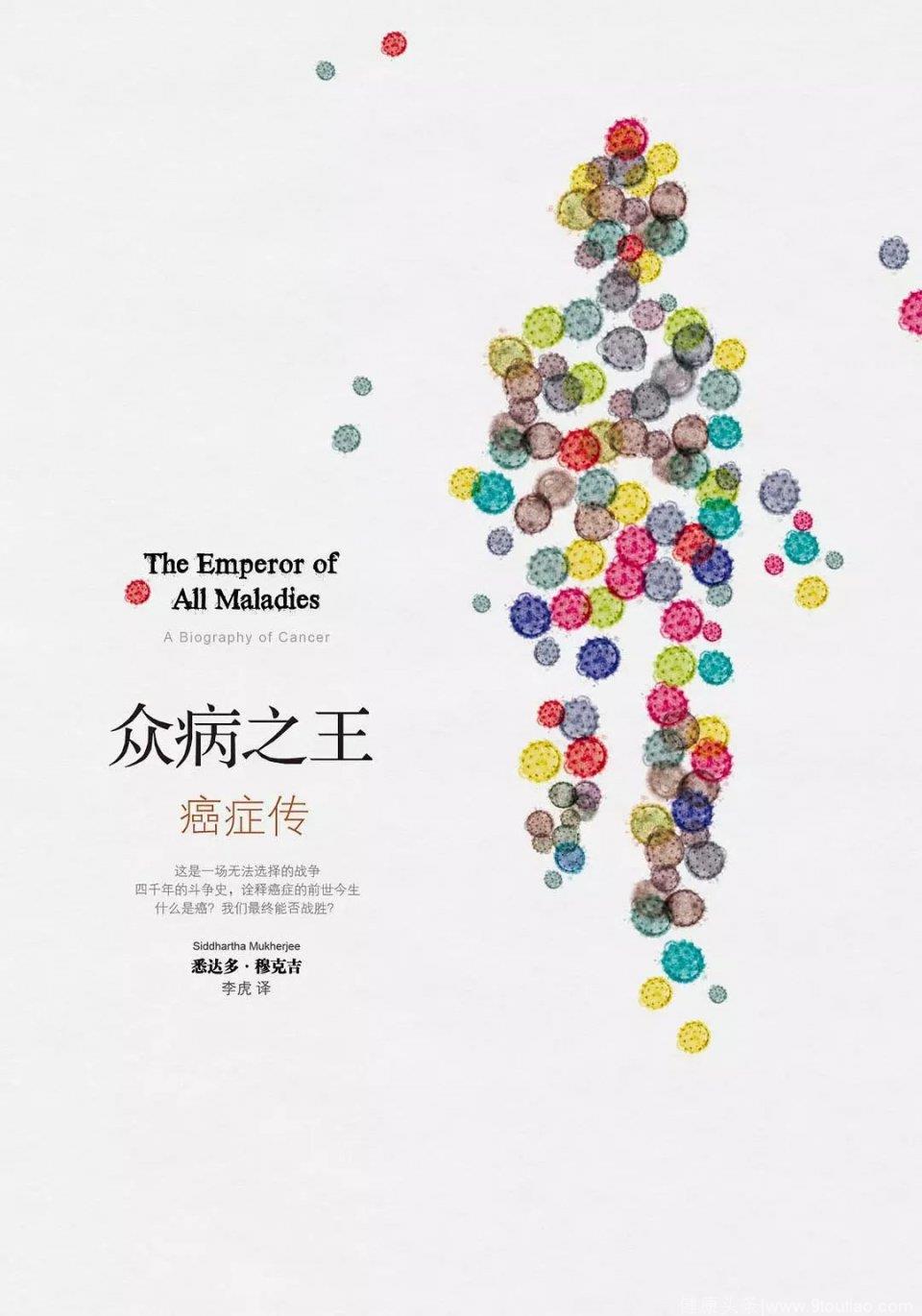
《众病之王》
作者: (美) 悉达多·穆克吉
译者: 李虎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3年2月
作者历时六年,以历史资料、专业文献、媒体报道、患者专访等信息,向读者阐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对抗癌症、预防癌症的斗争史。
丹尼斯经常梦见自己被吸血鬼追赶,这显然象征着他正被死亡追赶。他总是在吸血鬼抓到他之前惊醒,但是有一天,他的梦做出了一个不同的结局。吸血鬼抓住了他,用尖牙利爪撕咬着他的血肉。丹尼斯大叫着醒了过来,惊出了一身冷汗。直到现在,他才想通自己从中领悟到了什么:
“我现在意识到,自己不只害怕死亡,还害怕那会很痛苦。”
丹尼斯担心自己长有不同的肿瘤,不会死得那么平静。有一回,肿瘤压迫到了他的神经,令他痛不可当。直到我与他的肿瘤医生制定出一个详细的计划后,他才感到放心了一些。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希望能注射足够剂量的止痛剂来去除所有的痛苦。他知道大剂量的止痛剂可以带来平静,甚至可能会让他停止呼吸。
2
对孤独的恐惧
我们害怕死亡带来的痛苦和虚无,也常常担心会孤独地面对死亡,就像《伊凡·伊里奇之死》一书中描述的那样,面对如此可怕的环境,我们会害怕临终时没有人来安慰自己。托尔斯泰将这种死亡称为“庄严而令人敬畏的死亡”。这种孤独感常常比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折磨人。
有一天,医院让我和一位病人的妻子谈谈,因为她“烦透了”。她不断向护士和实习医生问问题,提要求,叫他们对丈夫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她扯起嗓子在走廊里大喊,打扰到了其他病人。这位叫黛博拉的女士和她的丈夫保罗今年都是42岁,他们曾经一起在一所最好的商学院念书,品学兼优,后来都成了颇有雄心的贸易商。
当我走进保罗的病房时,他看起来很可怜,黄疸使他深陷的脸颊更显得虚弱。在我们互相介绍的时候,他的手紧张地搓弄着床单。他认为自己能够康复。他必须保持乐观,直到最后。但是他有没有担心过结果也许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呢?他沉默了半晌,然后说他经常这样想,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因为他的妻子会受不了。
我为保罗和黛博拉感到深深的悲痛。他们是那么用心地保护对方,以至于最终阻止了对方谈论那些最令他们害怕的事。对他们俩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孤独感!我和保罗谈到了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在一起时最幸福的回忆,还有犹豫很久之后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
延伸阅读:医学与癌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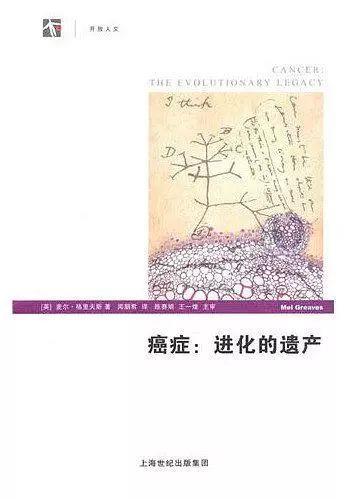
《癌症:进化的遗产》
作者: (英)麦尔·格里夫斯
译者: 闻朝君
版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2月
作者认为癌症并不是新生疾病。尽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癌症的主要类型和发生率不尽相同,但它在自然界普遍存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远离癌症的乌托邦。
3
对拖累别人的恐惧
比起被人照顾,我们通常更习惯去照顾别人。而且我们一般都很自信能照顾自己,身体慢慢衰弱直至死亡的念头之所以会使我们害怕,还因为这会使我们不得不极度地依赖别人,而与此同时,我们却什么也给不了别人。
然而,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还有一个生命中最伟大的仪式需要我们去传承。我们每个人对死亡的认识通常都来自于自己曾经见过的例子,如祖父母的死、父母的死、兄弟姐妹的死,还有好友的死,等等。当轮到自己时,这些场景就成了我们的指引。
我有幸也曾有过这样一位重要的导师——我的祖母。她是一个含蓄的女人,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但是在我那看似艰难的童年的每个阶段,都有她的身影。后来我长大后又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穿着一件很干净的睡衣,美丽而安详,我和她都知道告别的时候快要到了,我握着她的手,鼓起勇气告诉她,她对我这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有多重要。当然,我哭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她用手指沾了一滴我的泪水,温柔地笑着说:“你知道,对我来说,你的眼泪和话语,就像金子一般珍贵,我会带上这些的。”我至今仍记得她最后几天的样子,尽管她已经不能自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
延伸阅读:医学与癌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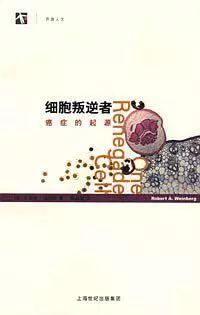
《细胞叛逆者》
作者: 罗伯特·温伯格
译者: 郭起浩
版本: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年5月
关于癌症的形成与起源。
4
对丢下孩子的恐惧
在所有对死亡的恐惧中,我常常觉得最可怕的是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对无法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恐惧。45岁的莱斯利有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一个12岁,一个13岁。她的卵巢癌已经转移,第二次化疗没有起到效果,医生告诉她,她只有6个月可活。她最不安的就是会丢下两个孩子。在努力帮她克服这种恐惧时,她具体描述了想象中自己死后孩子们最糟糕的情况。
首先她把自己看作一个幽灵,能看到孩子的生活,但触摸不到他们也不能和他们说话。孩子们伤心失落,她却无能为力。一想到这些场景,莱斯利就会感到胸口郁闷难当,以至呼吸困难。我建议停止治疗,但她还想继续。然后,她看到女儿正在为她的大提琴表演做准备,莱斯利以前常常陪着她参加这样的音乐会。现在,小索菲不得不一个人去了,她坐在演奏台上,完全不知所措,塌着肩膀,眼神空洞。想到这些,莱斯利的脸变得更加扭曲了,我开始怀疑这次治疗是否会有害无益。但就在我准备打断她的时候,她看见女儿笑了。她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心思:“妈妈不在这儿,但是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总是在这里陪我的情景......我脑子里听得到她说的话,还有她的鼓励。我能感到她在背后支持我,我的心能感受到她的爱。好像现在她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陪着我。”然后莱斯利看到女儿带着深沉而成熟的情感演奏起来,和以前完全不同。
两年后,我收到了莱斯利的信,她还活着,还在接受治疗。她回忆说这次治疗是她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刻之一。但是这次治疗驱走了她的恐惧,使她收获了自信,让她能够继续与疾病抗争。
延伸阅读:个人抗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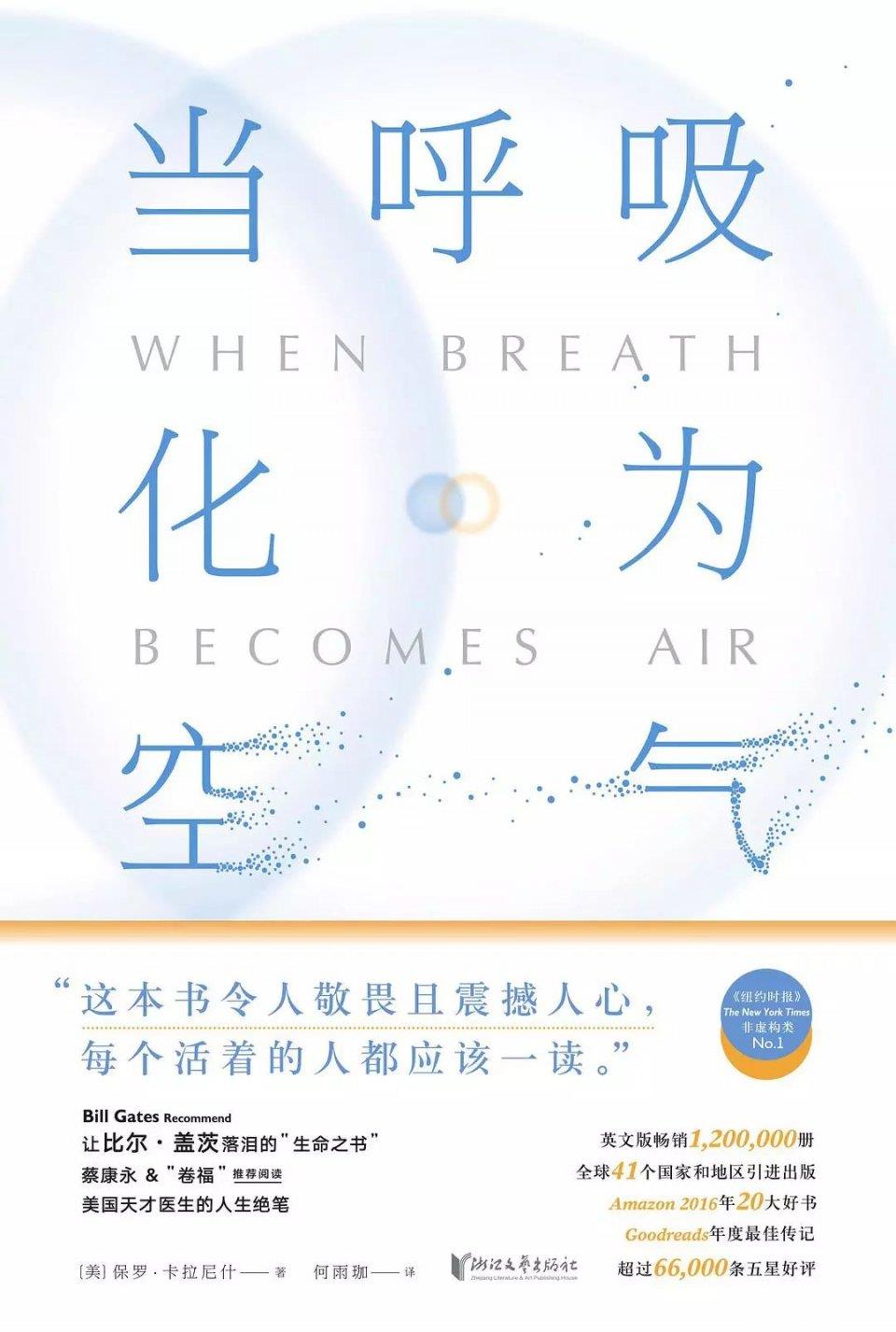
《当呼吸化为空气》
作者:(美)保罗·卡拉尼什
译者:何雨珈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作者获得过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2013年,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点击书封,查看关于该书文章《面对死亡,对“活着”这件事更加笃定》。
5
对未尽之事的恐惧
死亡即是永别。为了走得祥和,我们须得与一切告别。事实上,要舍弃我们未能实现的抱负、旅行的梦想或者曾经珍视却很快夭折的爱情,并不容易。通常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去做最后的尝试。写下自己一直想写的诗句,做一次梦寐以求的旅行,趁着一切还有可能的时候。因为这是最后的尝试,所以即使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那我们也不会有任何遗憾。但是,最难释怀的往往是那些深深刻在我们生命中的痛苦情感。
36岁的珍妮弗得了一种侵略性极强的乳腺癌,任何治疗都没有效果,她即将离开人世。6岁的时候,父亲抛下她和11岁的哥哥,移居墨西哥,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他们。在给他写信之前,珍妮弗犹豫了很久,离开30年了,他还会感到羞愧吗?他会不会漠不关心甚至连信也不回?但是死亡的庄严时刻常常会叩开最冷酷无情的心门。珍妮弗的父亲来了,虽然感到害怕和羞愧,但他还是来了。这是珍妮弗成人后与父亲的唯一一次谈话,她终于可以告诉父亲自己希望能了解他,希望父亲能保护她,把他生活中所知道的教给她。
她给父亲看了自己的照片,那是一张她患病之前的照片,依然光彩照人,还有她儿子的照片。面对着她憔悴的身体和面庞,他无心为自己辩解,只是听着,最后对她说了对不起。他说他那时焦虑不安,如果是今天,他不可能这样做,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他祈求她的原谅。不久后,珍妮弗就平静地病逝了。
延伸阅读:个人抗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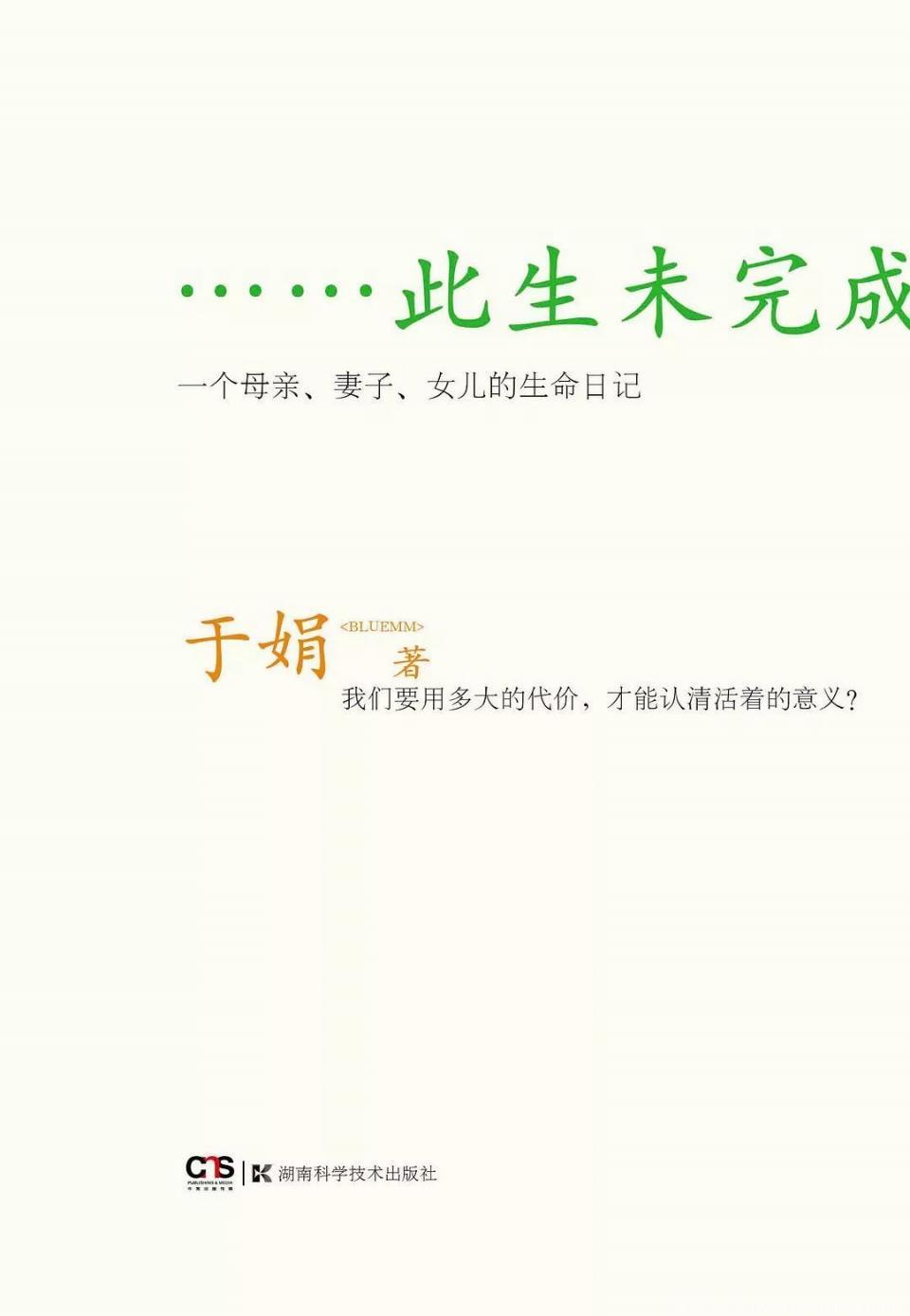
《此生未完成》
作者: 于娟
版本: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1年5月
一个母亲、妻子、女儿的生命日记:“我们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认清活着的意义?”
“虚假的希望”,还是意识的力量?
医生,尤其是肿瘤医生,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不要给病人虚假的希望”。我们都知道,对一个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要比被医生欠考虑的承诺所欺骗更痛苦的了。还有一种危险是,某些病人会天真地相信这个希望,因为这些自然方法,他们有可能会继续抽烟、不去做乳房X射线扫描或是拒绝做化疗那样艰难的治疗。出于这些合理的担忧,我的同事有时会拒绝采用所有超出常规的疗法。
不过归根结底,这会将我们局限在一种让每个人的自我抵抗能力都受到抑制的医学理念里。就好像面对癌症时,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无论是在病前还是病后。鼓励这样的被动行为其实是在创造一种绝望感流行的文化。
更糟的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绝望感,因为一切科学证据都表明,我们能够通过深刻影响自身的抵抗力来解除癌症机制带来的危险。这正是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在那份产生巨大反响的报告中所强调的。
这份报告指出:
“在原则上,大多数癌症都可以预防。”
我个人已经不再屈从于这种虚假的绝望感,它使我情绪消极无所作为。写作这本《每个人的战争》时,我无意向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强行推荐改变生活方式的办法,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情况的方法。不过,我选择了分享,与每一个想知道怎样才能更积极地促进自身健康的人分享我的经历,还有我从科学文献中学到的一切。
这些主要方法,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体势”的重要性;自然之力的协同作用;意识的效用。

作者在演讲。图片©amessi.org
我发现,几乎所有寿命超出统计学预期之外的癌症患者都有着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是的,我也许会比预计的更早去世,但是我也有可能比预计的活得更久。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从现在起尽可能地好好活着。无论最后发生什么,这都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体势”的重要性
我的藏族同行毫不否认在紧急情况时,西医有着神奇的效果,西医会针对具体的疾病采用特定的药物或疗法。多亏了阑尾切除手术、治疗肺炎的盘尼西林和应对急性过敏反应的肾上腺素,西医每天都在拯救着生命。
但是当治疗慢性疾病时,西医的短处很快就暴露出来。癌症是典型的慢性病。想通过全力发展新的检测和清除肿瘤的技术来消灭癌症不太可能。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得照顾好“体势”。正如世界癌症研究基金2007年度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加强身体抵抗机制的方法,如营养学和身体锻炼,确实能起到预防癌症的效果,并对治疗癌症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些方法靠的是自然作用,所以消除了预防和治疗之间的界限。
一方面,这些方法能够阻止我们所有人都携带的微肿瘤发展成肿瘤(预防);另一方面,这些方法能强化手术、化疗和放疗的作用,防止复发(治疗)。
每个人都会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患有癌症,有时候是很严重的癌症,但他们的肿瘤经过治疗后便退化了,有的人从那之后就一直正常地生活着。有时候,扫描还发现他们的肿瘤变小了。不管怎样,这些患者的自然防御力现在已经抑制住了癌症,使其无法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正如发现血管生成现象的犹大·福克曼在《自然》杂志上所写的那样,这些人患着一种“无病状的癌症”。
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度过,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界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发现了第一种用于医学的抗生素,还发现了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成了一位积极的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一直认为科学医疗的唯一问题是它还不够科学,只有当医生和患者都学会了用自然的治愈力量来驾驭身心之力时,现代医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医学。”
延伸阅读:个人抗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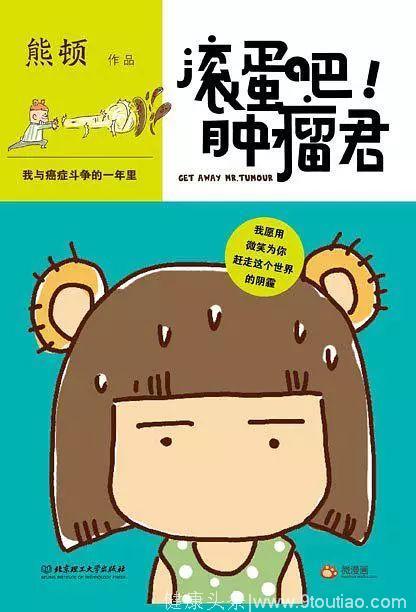
《滚蛋吧!肿瘤君》
作者: 熊顿
版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在睁眼就是治疗室,入耳就是化疗、吃药、体温、白细胞增减的环境里”,作者记录了自己的每一段经历,用画笔捕捉了来自父母、亲人、朋友的关怀和生活中的点滴感动。
自然之力的协同
身体是一个处于平衡的巨大系统,每一种功能都与别的功能相互作用。改变其中的一种,整体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从哪里开始:是饮食,身体锻炼,心理练习,还是其他能让你的生命更有意义、使你更具生命意识的方法。
每一种病情、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防治癌症的方式也独一无二。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生存意志。有些人通过参加合唱团或看喜剧来培养它,有些人则通过写诗、记日记或是更多地与自己的孙儿们待在一起来做到这一点。
提高人对某一方面的认识似乎也可以自动提高人对其他方面的认识。例如,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发现,多吃蔬菜、少吃动物蛋白的老鼠运动也变多了,就好像饮食的平衡更容易使老鼠从事身体锻炼一样。同样的,冥想或瑜伽练习也与身体的意识相联,久而久之,我们会失去对非平衡饮食的兴趣,非平衡饮食加重了我们胃部的负担,总体上也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也会丧失对烟草的兴趣,烟草带来的影响要比饮食具体一些,它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加速心率,就像烟草留在我们头发和指间的气味那样清晰可见。我们还会不那么爱喝酒了,酒精会让我们不能清楚地思考,动作也变得不利索,这种效果更加显而易见。健康是一个整体,每朝着更为平衡的状态走一步,下一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延伸阅读:个人抗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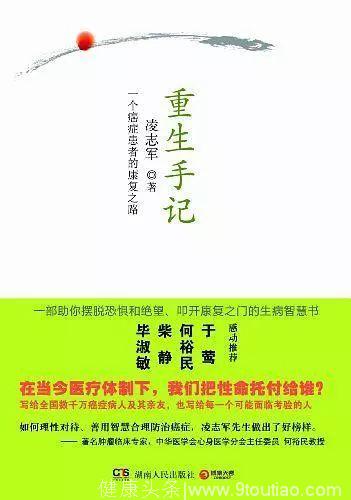
《重生手记》
作者: 凌志军
版本: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一位癌症患者的抗癌亲历记。
意识的效用
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利用癌症知识的革新来防治癌症和照顾自己。但是这首先需要我们革新自己的意识。最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美丽和价值。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的生命,呵护它,就像呵护一个信任我们的孩子一样。这种意识使我们的生理机能不致遭到破坏,癌症不易发生,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切事物来滋养和支撑我们的生命力。
要开始真正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理解生命的美丽,身患癌症不是必要条件。相反,我们离生命的价值越近,对生命那充满生机的美丽越敏感,我们就越容易预防癌症,也越有可能从生命的旅程中受益。
我们所有人都受到生命意识缺失的困扰,对那些异常贫困者更是如此。恢复全球性的环境平衡将减少这种极度不公的社会现象。因为最底层的人群同时也是患癌率最高的人群,他们最容易受到工业势力的伤害,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不得不吃最便宜的食品,也是最不健康(糖分最高,ω-6脂肪酸含量最高,反式脂肪最多)、受杀虫剂污染最严重的食品。而在工作中,他们又最容易暴露在会诱发癌症的产品之中(墙壁或地板涂料、油漆、清洁剂等)。至于他们的住所,则主要集中在污染最重的地区(靠近锅炉厂、有毒的垃圾场、冒烟的工厂等),他们暴露在工业垃圾之中,使自身的免疫系统压力重重。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是最突出的受害者,是一群最需要利用自然方法抵御这些致癌因素的人,但是他们也是最难获得这些方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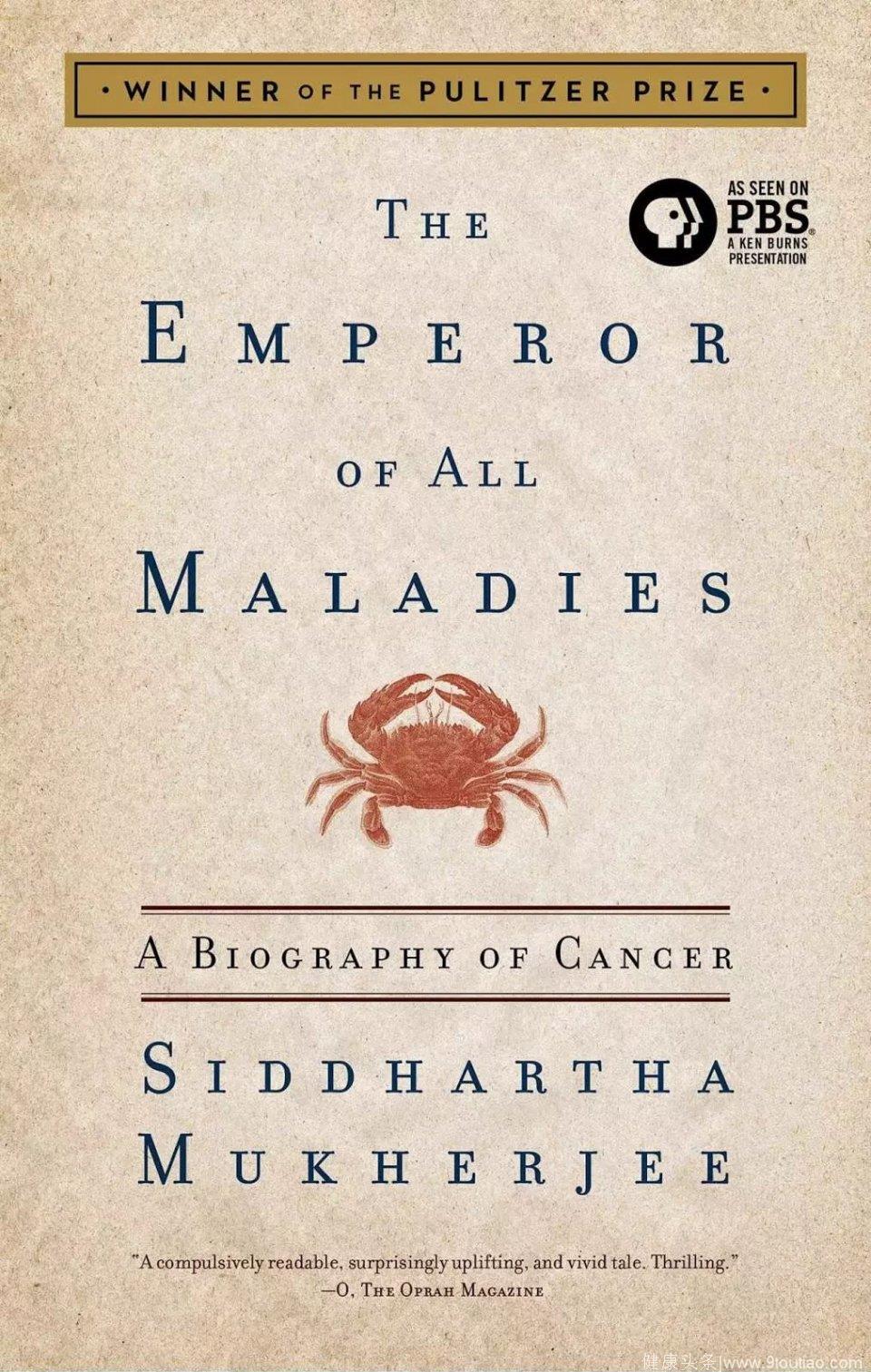
纪录片《癌症:众疾之皇》(Cancer: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2015)海报。
本文内容经“理想国”授权整合自《每个人的战争》(作者: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译者: 张俊;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一书第一、四、十及十三章,内容有删节、顺序有调整,标题为编者所取。整合与编辑:西西。题图素材来自《抗癌的我》(50/50 ,2011)剧照局部。未经出版方或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