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华人科学家做出两项被认定会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可能治愈癌症
对于张峰,很多人最先注意到的是他比较年轻,有关他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提到了这一点。他年仅36岁,带着眼镜,还有一张比实际年龄更显小的圆脸。这位生物学家已经做出了两项被认定会赢得诺贝尔奖的发现。
张峰成为科学界明星是因为发现了基因编辑工具CRISPR,它可以对人类DNA进行精确修改。CRISPR受到热烈推崇,被认为可以治愈遗传病、疗治癌症,还有可能用来的“定制”婴儿。
CRISPR还引发了博德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间激烈的专利纠纷。张峰在博德研究所工作,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作出了有关CRISPR的早期重要发现。专利之争点燃了这项科学突破真正归功于谁的争论。
近日,在致力于讨论CRISPR技术众多应用的CRISPRCON大会上(张峰是这次大会的主题演讲嘉宾),《大西洋月刊》记者Sarah Zhang采访了张峰,请他谈了谈这项技术的未来。以下是采访实录(有删改)。
 莎拉:你最初是怎么对生物学产生兴趣的?
莎拉:你最初是怎么对生物学产生兴趣的?张峰:我最初不喜欢生物学,感觉这门学科就是辨别不同的叶子,给东西分类。我更喜欢数学、化学和计算机——把东西拆开,再重新装回去。
莎拉:这不就是你用CRISPR所做的事情吗。CRISPR最初来自于细菌,那些细菌利用它来切割DNA,被研究细菌的科学家首次发现。你把它放入人类细胞,发现它也能切割DNA。你是否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晦涩难懂的微生物学文献?张峰:谷歌是不错的工具,PubMed生物医学文献检索系统也很好,你可以搜索不同的东西。我寻找东西的方法是,先提出某个假设或想法,接着搜索与那个假设有关的东西,然后大量阅读那个领域的文章,看看有没有什么内容涉及到我的研究课题。
莎拉:你读高中时,曾在一间基因治疗实验室工作过。基因治疗拥有令人注目的发展历程。(基因治疗把正常基因插入到基因存在缺陷或异常的人身上;CRISPR从理论上来说可以用来插入、删除或修改现有基因。)基因治疗在上世纪90年代大受追捧,后来陷入低谷,现在基因治疗终于获得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你是否关注过这些?你是否从中看到了CRISPR的未来?张峰:是的。我在某个星期六的分子生物课上首次听说基因治疗。那是1994年或者1995年。基因治疗的潜力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能从基因层面上治疗疾病,那么我们能治疗很多东西。
我读高中的时候,得梅因恰好有一间基因治疗实验室招收志愿者,所以我高二时开始在那里工作。我接触到了基因治疗的各种方法。
基因治疗的一大挑战是导入。我们如何让起治疗作用的基因进入不同的组织?那时,实验室里有人研究各种各样的病毒载体,比如莫洛尼氏鼠白血病病毒、单纯疱疹病毒、腺相关病毒和腺病毒。这些都是人们为了让药物进入患者体内而探索过的不同方法。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令人非常兴奋。
后来在1999年,曝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事情。
莎拉:你是指杰西·吉尔辛格(Jesse Gelsinger)在临床试验中死亡。用来插入基因治疗的病毒引起严重免疫反应,导致他死亡。张峰:这对基因治疗研究领域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时刻。那时,我们对导入系统的了解不够全面,对那些病毒的生物机理认识不足。这方面的很多知识也被用于基因编辑。
 莎拉:在你看来,用CRISPR来治疗人类疾病的挑战是什么?
莎拉:在你看来,用CRISPR来治疗人类疾病的挑战是什么?张峰:我们掌握的导入系统类型还很有限。对于很多疾病,我们没有合适的导入系统。目前,我们能进入血液细胞和眼睛,可能还有耳朵。但如果想在全身层面做点什么的话,我们尚未找到好办法。
病毒是把东西导入细胞的天然方法。这是一个办法,所以我们对此进行研究,同时探索以前没有被用于导入的其他多种病毒。我们也着眼于外泌体,这是细胞分泌的囊泡,能够在细胞之间传递信息。
莎拉:也是天然的方法。张峰:也是天然的方法。我们还合作研究脂质纳米粒,也就是脂质体。我认为,我们必须广撒网,以便全面地解决问题。不同的组织很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法。
莎拉:哪些器官是CRISPR最难进入的?张峰:我非常希望可以进入大脑。但基本上没什么选择余地。你必须研究基本的生物机理,弄明白自然想让我们去哪里。
莎拉:说到大脑,你的实验室已经因为CRISPR而获得了大量关注,但你也在研究大脑,特别是精神障碍。张峰:我从读大学起就一直对大脑感兴趣。大脑决定了我们是谁,不幸的是,我们对大脑知之甚少。我在大学里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患上了一种精神疾病。从那段经历中,我认识到精神疾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并不是真正了解精神疾病,而且问题在于不仅仅是患者本人倍受痛苦。如果我能更多地了解大脑,或许就能找到办法帮助那些人。
莎拉:精神障碍可能是我们对生物机理的了解和生物机理的影响之间差距最悬殊的生物学领域。张峰:没错,正是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大脑的复杂性。不同的细胞太多了,不同的细胞类型太多了。很难对大脑进行研究,因为它被颅骨包裹,而且是一个大的、致密的组织。很难窥视这个组织的内部,了解它是如何运转的。另外,分子和信号非常细微,使大脑研究充满挑战性。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新的技术和工具来分析不同的细胞和不同的分子,研究它们如何作为大脑中的一个系统协同工作。
莎拉:你如何利用CRISPR来研究大脑?张峰:通过DNA测序,科学家已经识别了很多基因变异,某些变异与大脑疾病风险升高有关。因此,我们建立小鼠动物模型,利用CRISPR来了解那些变异是如何工作的,它们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大脑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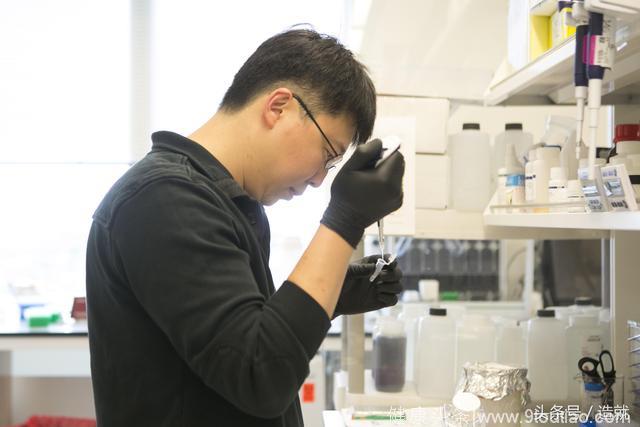 莎拉:患者是否给你发了很多邮件,想知道CRISPR可以如何帮助他们?
莎拉:患者是否给你发了很多邮件,想知道CRISPR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张峰:是的,几乎每天我都会收到他们的邮件。患者真的很想了解这项技术。他们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好让他们更快得到治疗。收到这样的讯息真的令人振奋鼓舞。那些邮件每天都在提醒我,有可能研发出可以帮助人们的东西,加快研究,好让我们更早地实现目标。
莎拉:但这是不是也很难?因为正如你所说,还存在所有那些挑战,你可能不得不对一些人说短期内不行。张峰:那些邮件提醒我们,我们处于这个非常幸运的位置,能够做出积极的改变。我觉得这很好。我们不应该把事情搞砸。
莎拉:CRISPR应该归功于谁?张峰:我认为应该归功于很多人。CRISPR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很多人参与了不同的阶段。一些人在早期发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后其他人接过接力棒,继续研究基本的生物机理。这就是科学发现的魅力所在。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万事万物、历史和文明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一次垒一块砖。
莎拉:你的一些科学家同行已经开始谈论使用CRISPR的潜在风险,比如凯文·埃斯维特(Kevin Esvelt)谈基因驱动和詹妮弗·杜德纳谈CRISPR应用于人体。你是否觉得自己处于道德权威的位置,因为你帮助实现了这项技术?张峰:我认为,我们都有责任,科学家、媒体、政策制定者、生物伦理学家都有义务参与讨论。我认为,作为科学家,我们能帮助传达这项技术是什么,帮助解释它是什么,了解这项技术的潜力有多大。
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是如何把CRISPR变成真正的治疗工具,以便治病救人。这离我们还比较遥远。至于“定制婴儿”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觉得更加遥远。我们对生物机理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没法想象那些东西会是什么。目前,我们连导致镰状细胞病的基因变异都治不好,哪怕一个变异都搞不定。
翻译:于波
校对:Lily
编辑:漫倩
来源:The Atlantic
造就:剧院式的线下演讲平台,发现最有创造力的思想点击蓝字“了解更多”,获取更多「造就」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