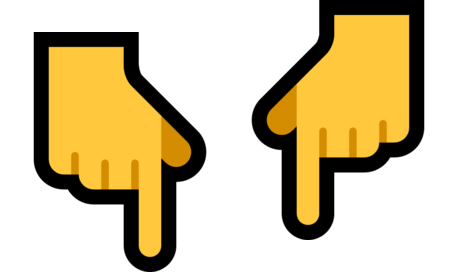黄洁夫:疾控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
CDC专业技术人员要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担当的科学精神与风骨,国家应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

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 张华东摄
17年前,一场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肆虐全国。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亲临一线,指挥抗击非典。
17年后,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袭来,并在世界暴发。如今,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的黄洁夫密切关注新冠疫情的发展,对疫情建言献策,并坚持每周在协和医院从事外科临床工作。
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3月20日,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黄洁夫。
专访黄洁夫:搞疾控的人是“战士”,他们的权威是技术,而不在级别。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谈SARS
领衔第二批专家组,支持钟南山病毒说新京报:2003年SARS期间,你在卫生部做什么工作?
黄洁夫:十七年前的事,仿佛还是昨天,记忆犹新。我是2001年10月调至卫生部的,2003年2月7日我回广州过年,8日广东省副省长与卫生厅长告知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山医科大学附二院发生了医务人员群体性不明原因肺炎,医疗界有些紧张。我第一时间就电话报告了卫生部主要领导,卫生部高度重视,春节前就派遣卫生部与国家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赴穗调查。第一批专家组调查结果是“衣原体”感染性肺炎,主要是当时发现尸检病理有大量衣原体。春节后,疫情未能控制,有更多人员发病,多个医院均发生疫情。我受命作为第二批专家组的卫生部领导赴广州。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基因测序、核酸检测等,病原体一直未明确,国家CDC专家与广州临床专家意见不一致,有“衣原体与病毒之争”。我是支持钟南山等八名呼吸病专家意见的,认为疫情是病毒感染。
新京报:这次新冠肺炎暴发后,你主要做了什么?
黄洁夫:常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为一名74岁的退休干部,虽已不能亲临抗疫前线,但心在抗疫前线,“老骥伏枥”吧!我有许多学生和昔日同事与朋友都在抗疫一线,我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也为他们英勇奋战取得的胜利而鼓舞,也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主要是在中国器官移植基金会层面,例如: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的同志们联合,联系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向大陆捐助了台湾第一批抗疫急需物资;基金会募捐善款,并与宜兴市人民政府、韩美林紫砂艺术馆捐赠紫砂壶义卖向抗疫一线的战友们献爱心;基金会开展了“网上讲座”,集中移植专家的智慧讨论与疫情有关热点问题,如:“终末期新冠病人肺移植”、“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疫后公卫体系重建等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
谈“短板”
新京报:与2003年SARS相比,你觉得这次应对疫情比较大的进步是什么?
黄洁夫:经过SARS以后我国综合国力与十七年前已今非昔比,我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科学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令全世界瞩目的是我们用了很短时间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是传染源,并在2020年1月10日,把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全世界分享,对传播途径有较明确判断,在检测、诊断和治疗新冠病毒方面均有较大进展。重组疫苗现已进入临床试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建成使用,以及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英勇赴疫情最前线,全社会万众一心抗击疫情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新京报:与2003年SARS相比,哪些方面变化很小或没有改变?疫后改革有什么建议?
黄洁夫:与社会经济及科技显著进步相比较,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的制度、体制与能力的现代化管理改革十分紧迫,这次新冠疫情深刻地反映了这些“短板”。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决策与我们体制的强大,则疫情牺牲会更加严重。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会在疫情控制形势进一步好转时审时度势地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并推进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
至于疫后改革,有人建议将CDC权力提升,我认为疾控工作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是采用科学方法对各类传染病、流行病开展监测,系统分析、风险评估、预警和干预,并制定标准和指南,是种专业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权力的提升是在于技术工作不受行政干扰的权威性,而不是行政级别的提升。如果将疾控技术人员官员化,疾控工作则有极大风险。国家CDC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地方CDC与地方卫健委疾控部门的行政关系和专业领域责任应该厘清。应完善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的直报系统,及时客观地反映临床一线医务人员的科学报告,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脱节的两张皮的老大难问题要解决。
CDC专业技术人员要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担当的科学精神与风骨,国家应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要明确重大疫情问题处理的责任、越级申诉的权利和渠道,以及失职渎职的责罚机制。

3月20日,黄洁夫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谈新冠患者肺移植
希望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硬核技术新京报:你如何评价一些国家政府提倡的“群体免疫”抗疫模式?
黄洁夫:“群体免疫”应该说是个伪命题,英文中的Herd immunity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中形成的“免疫屏障”的理论与概念,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医学院就学过的老理论,是 “物竞天择”。如果今天在抗击疫情中采用自生自灭的“群体免疫”,实际上是向病毒投降。会造成大量病人的死亡与社会动乱。这种观点是对人类医学进步的否定,也是不尊重人权。有些政府巧用这个概念,威慑公众,让公民自觉隔离,实际上也达到封城、封国的目的,现在尽管说有不同的模式,但实际上除了隔离还是隔离,只是分层、分级、分期的隔离而已,在疫情与经济损失中找平衡。不少国家的疫情失控,十分惨烈。我们移植圈有不少专家都认识到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幸运与自豪。我国的新冠疫情作为甲类管理,诊疗所用的试剂、中西药、呼吸机、ECMO(体外膜肺氧合)都充足供给,甚至对有一丝希望的病人都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例如:采用肺移植,降低死亡率。
新京报:最近无锡市人民医院和浙江大学第一医院做了几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术,引发各界关注。对此你怎么看?
黄洁夫:对烈性传染病进行器官移植是世界医学的禁区,肺移植技术已是成熟的医疗技术,但如何在新冠肺炎中使用则是全球关注的热点。我国提出进行高选择性、高防护性、严管控性的肺移植以降低新冠死亡率,这使世界移植协会(TTS)与世卫组织器官移植特别工作委员会(WHO Task Force)十分关注。最近世界移植协会(TTS)与WHO与我联系,希望我国介绍在疫情中如何推进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经验。所以对此项工作我国应有统一指挥,选择前期已有扎实临床工作基础的团队进行临床研究,切忌一哄而上,合理与符合伦理标准地利用爱心奉献的器官来源,并要评估与科学总结及随访,并由有扎实专业外文基础的专家予以总结,形成为世界所认可的中国抗疫的硬核技术。
谈病毒起源
世界人民都需要一个更详细、更透明的解释新京报:现在国内外均热议新冠病毒来源,你有何见解?
黄洁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我们的“云播间”由武汉同济大学陈忠华教授根据国内外文献做了较全面的一个报告,你们可以上网参考。我只是一名临床外科医生,隔行如隔山,这个问题应请病毒学家来回答更妥当一些。但现在国际上有别有用心的人借助疫情污名化中国,我是十分愤慨的,病毒来源是一个生物界的自然过程,应该科学地研究,更不能带上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是明显违反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疾病与病毒命名原则的。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现有一些反华势力企图将新冠疫情变成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我们应坚决回击,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要应用科学的事实与围绕这一次新冠疫情流行病学,病毒演化树中的种种疑问,实事求是地反击。
2002-2003年SARS首先发生于佛山、顺德等周边农村,与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交易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关系链条清晰,又找到了零号病人,经过近三年时间的努力才逐步明确从蝙蝠到市场野生哺乳动物再传人的关系。但武汉市居民较少有吃野生动物的习惯,目前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或人类的直接感染源仍未明确,零号病人不清楚。再加上国内外许多病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或武汉毫无联系,围绕疫情发生的去年在国外11月-12月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事件。所以我认为应请世界卫生组织(WHO)牵头在全球范围内调查研究,应该发挥我国曾经参加过中美合作冠状病毒研究的病毒学与流行病学专家的作用,与世界科学家一道得出可信的科学结论,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得到一个更详细、更透明的解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世界应该感谢武汉人民”,我认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新京报:你怎么判断现在我国与全球疫情形势?
黄洁夫:目前全世界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都还不够,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不能够毫无科学依据轻易对疫情发展形势做预测。我国的抗疫由于有国家体制的优势与全社会的热烈响应及医务人员高尚的职业操守,我们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看到了希望曙光。但随着全球疫情的恶化,如何防止输入性疫情成了艰巨的挑战,绝不能掉以轻心,新冠疫情长期化很可能是个事实。当前我国采取的严格隔离政策与全球的疫情发展、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了解结合起来,及时准确地将抗疫与经济社会恢复要做战略战术上的调整。另外,新冠疫情也可能给我国带来一次机遇,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国际竞争力及政治大国形象。至于全球的疫情形势我是不乐观的。COVID-19病毒与SARS病毒不同,它在人与人之间有很高传播速率,由于国家体制、文化、经济、宗教的不同,制约因素很多。目前全球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超过30万新冠肺炎病例,世卫组织称新冠肺炎 是“世界大流行病” (Pandemic)。这个大流行病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全球的政治与经济都将会产生严重影响并改变世界格局。
谈中西医之争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此次新冠肺炎治疗中民众与医务界对于中西药孰优孰劣的争议?
黄洁夫:中西医谁优谁劣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各有其优势。目前我国医疗服务是西医占绝对优势,建议不要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由于中医具有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属性,中医对某些疾病有明确疗效,国内民众普遍是肯定中医的。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发挥的作用与贡献记录在抗疫战场上,得到举世关注和赞誉。我建议中医应根据中医理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个中医的学术命名,不能跟随西医也称COVID-19,是否可称之为“庚子时疫”,根据不同地域和气候特点,又分“温湿”(湿热)、“寒湿”。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中医治理瘟疫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经验,应予以总结与提炼。
我记得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十余年前访问北京时曾给部级领导作过一场世界科技进展瞻望的报告,讲到未来的医学应发挥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辩证施治的个性化以及内外兼治的特色。他讲,中西医准确讲法应该说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疗。他说未来应该是One world, One medicine(一个世界,一种医学)。
我国中医专家应阐明在抗疫中怎样扶正祛邪、化痰清热、宣肺败毒等,使新冠肺炎可以预防,使轻症不成为重症,使重症转为轻症,怎样配合西医救治危重病人,并要有准确的英文翻译与术语,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与方式讲好中医的故事。中医药制药业应该将现在疫情中已证实的中医药方剂变成符合世界食药规格的产品,如:片剂、冲剂、胶囊剂,并备有英文的成分说明与安全性保证,使中医药为世界抗疫发挥作用,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迈出坚实的一步。应该把此次抗击疫情看作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黄金时机,不争论,不折腾,做实事。老子曰“胜人者力,胜己者强”,中医的强大必须依靠中医医务人员的自强精神。
新京报: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医的一些“非议”?
黄洁夫:我是学西医的,但我并不否定中医,生病时有时也找中医诊病,2017年我去梵蒂冈参加一次世界移植会议前身体不佳,就专程去广东省中医院住院了一个星期。世界上有不少华侨包括外国朋友也看中医。但不可否认,我国的中医医务工作者需要自强。例如我国中医院西化现象很严重,中医药大学教育中中医课程薄弱,中医学校毕业生报考西医的研究生比例过高,从事中医的学生专业思想不牢,中青年知名中医专家太少。中医也用大白鼠作动物实验发表论文,申报基金和奖项,中医大夫诊病都要看化验单和CT(计算机断层扫描)、MRI(核磁共振成像)、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报告单,中医的“脉诊”与许多行之有效的中医疗法已差不多失传,名中医后继无人。民间中医生存空间很小,特别是那些世代传承确有专长,实践中又得到广大民众认可的民间的中医学偏方、祖传方是可贵的遗产,要进行抢救性挖掘和扶持。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祖传的中医也能够合法地行医和教育传承,同时也要加强监管,要防止泥沙俱下,假冒伪劣的江湖巫医,莆田老军医损害中医声誉危害群众。
 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新冠疫苗取得节点性突破,上市最快得明年
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新冠疫苗取得节点性突破,上市最快得明年 金银潭“留守”医生:尽可能把危重病人死亡率降下来
金银潭“留守”医生:尽可能把危重病人死亡率降下来 留守意大利:“封城”后,4名华人的防疫日记既然在看,就点一下吧
留守意大利:“封城”后,4名华人的防疫日记既然在看,就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