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病人哭泣时,医生能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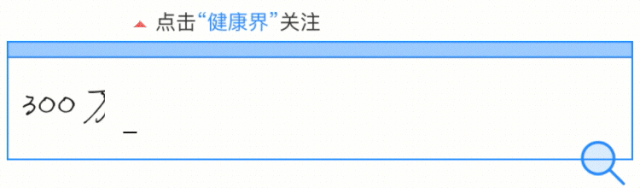 “
“行医中最难的不是癌症的诊疗,而是如何面对哭泣的患者。
”如果诊断结果是最坏的情况,医生该怎么告知病人结果?面对伤心哭泣的癌症病人,医生们的内心自白又是怎么样的呢?虽然曾在四个国家进行医学教育、培训、研究和临床工作,但Bishal Gyawali依然被这些问题难倒了。对他这个肿瘤学家来说,行医中最难的不是癌症的诊疗,而是如何面对哭泣的患者。目前加拿大皇后大学癌症研究所(Queen's University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的Bishal Gyawali将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出来,他发现,如何面对患者并无既定路径,而是需要根据患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等调整方案,而这也正是医生行医的美妙之处。以下为Bishal Gyawali的自述: Bishal Gyawali, MD, PhD在并不算长的医生生涯中,我曾在几个不同的国家工作。早先,我在故乡尼泊尔的医学院学习。2012年,我去日本接受癌症治疗方面的培训。2017年我重回尼泊尔,成为一名癌症专科医生。2018年,我远赴美国波士顿进行癌症政策相关方面的研究。而从2019年年初至今,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Kingston)开启了新生活。在新国家开展医疗工作总是充满挑战,不仅因为医疗系统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对治疗的影响也是挑战的重要一环。现在我正在加拿大皇后大学癌症研究所专攻癌症临床治疗。对于治疗条例或者用药剂量等问题,我并不担心。癌症治疗方法瞬息万变,某些癌症的治疗方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翻新,我自信能够根据不同的症状对症下药,为病人提供最精准的治疗。但治疗只是一方面。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告知病人疾病详情。而另一难题,就是如何根据病人的个人情况和文化背景,将患病细节和盘托出。
Bishal Gyawali, MD, PhD在并不算长的医生生涯中,我曾在几个不同的国家工作。早先,我在故乡尼泊尔的医学院学习。2012年,我去日本接受癌症治疗方面的培训。2017年我重回尼泊尔,成为一名癌症专科医生。2018年,我远赴美国波士顿进行癌症政策相关方面的研究。而从2019年年初至今,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Kingston)开启了新生活。在新国家开展医疗工作总是充满挑战,不仅因为医疗系统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对治疗的影响也是挑战的重要一环。现在我正在加拿大皇后大学癌症研究所专攻癌症临床治疗。对于治疗条例或者用药剂量等问题,我并不担心。癌症治疗方法瞬息万变,某些癌症的治疗方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翻新,我自信能够根据不同的症状对症下药,为病人提供最精准的治疗。但治疗只是一方面。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告知病人疾病详情。而另一难题,就是如何根据病人的个人情况和文化背景,将患病细节和盘托出。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安德莉亚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批病人之一。她被诊断出结肠癌三期,需要辅助性化疗,我需要告诉她肿块不幸复发的消息。看到她和丈夫在诊所等候,我走向他们,先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接着聊了聊金斯顿的天气、彼此的家庭等种种日常。说真话令人于心不忍,但我必须要告诉她实情。我梳理了她治疗的过程,确保她明白为何要在手术之后做化疗,才对她说出诊断结果:癌症复发,并在肝脏和肺中扩散。曾经以为自己会康复的安德莉亚震惊了,抽泣起来。她的丈夫呆立着,眼中透出木然与绝望。这时候的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拉起她的手?给她一个拥抱?跟她聊聊转移癌细胞的治疗方案?或用免疫疗法给他们能够治愈的错觉?还是,静悄悄递给她纸巾,让她平静一会儿,待她和丈夫讨论之后离开诊所?当你的病人开始哭泣,你会怎么做?这真的是对医生的灵魂拷问。在加拿大开始工作时,这也是我最大的忧虑。我知道如何治疗癌症,但我不知道在通知病人患病噩耗(癌症复发,疑难杂症,需要转移至临终关怀等)的时候应如何表现。因此,当我的导师克里斯托弗·布斯(Christopher Booth)问我对于癌症诊所有什么问题要问时,我抛出我的问题:当病人哭泣的时候,医生应该怎么做?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了解到,在西方国家,大部分癌症医生会直面病人从治疗到恶化的过程,同时也会充分用语言和肢体接触安慰病人,表达对病人的同理心。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东方VS西方 在日本接受了5年度研究生培训后,我于2017年返回尼泊尔,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天,45岁的拉梅什(Ramesh)和他的哥哥来了我所在的诊所。他被发现有肝脏肿块,活检确定是转移性腺癌,CT扫描显示胰腺可能是主要病变部位。在尼泊尔,公立医院的肿瘤科非常拥挤,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因此不适合对病人说明病情等。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诊所,目前推崇的用于告诉病人“坏消息”的SPIKES方案不是很适用,因为第一步“安排隐私空间”就做不到。在就诊期间,我告诉拉梅什和他的哥哥,拉梅什患有胰腺癌。他们一听,吓坏了,哥哥停顿了一下问,“你确定吗?医生。”和很多病人一样,哥哥还补充道:“他又不喝酒又不抽烟,这怎么可能?”过了几分钟,我才鼓起勇气说癌症没法治好。拉梅什开始哭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我来说,这不是国外,这是尼泊尔,他是我的同胞,我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应该握住他的手还是拥抱他?但是我从没见过尼泊尔医生拥抱病人。哥哥问是不是去印度治疗会增加治愈的机会。其实我知道,不论他们花多少钱或在哪里寻求治疗,转移性胰腺癌都无法治愈,我是不是该鼓励他们这样做?这样我就不用再面对他们了。不,道德告诉我,绝对不能这样做。那我应该告诉他,我会给他化疗,可能可以治好他吗?不,也不行,我应该诚实,不要给他不切实际的希望。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东方VS西方 在日本接受了5年度研究生培训后,我于2017年返回尼泊尔,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天,45岁的拉梅什(Ramesh)和他的哥哥来了我所在的诊所。他被发现有肝脏肿块,活检确定是转移性腺癌,CT扫描显示胰腺可能是主要病变部位。在尼泊尔,公立医院的肿瘤科非常拥挤,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因此不适合对病人说明病情等。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诊所,目前推崇的用于告诉病人“坏消息”的SPIKES方案不是很适用,因为第一步“安排隐私空间”就做不到。在就诊期间,我告诉拉梅什和他的哥哥,拉梅什患有胰腺癌。他们一听,吓坏了,哥哥停顿了一下问,“你确定吗?医生。”和很多病人一样,哥哥还补充道:“他又不喝酒又不抽烟,这怎么可能?”过了几分钟,我才鼓起勇气说癌症没法治好。拉梅什开始哭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我来说,这不是国外,这是尼泊尔,他是我的同胞,我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应该握住他的手还是拥抱他?但是我从没见过尼泊尔医生拥抱病人。哥哥问是不是去印度治疗会增加治愈的机会。其实我知道,不论他们花多少钱或在哪里寻求治疗,转移性胰腺癌都无法治愈,我是不是该鼓励他们这样做?这样我就不用再面对他们了。不,道德告诉我,绝对不能这样做。那我应该告诉他,我会给他化疗,可能可以治好他吗?不,也不行,我应该诚实,不要给他不切实际的希望。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那天晚上,我和一位同事讨论了这个话题,问他怎么应对这种情况。他告诉我,病人及其家人希望我们坚强。显然,如果医生表现出明显的同情迹象,病人可能会认为预后要比实际情况差得多。尼泊尔的病人似乎更希望医生用偏“强硬”的词表达他们的关心,就像从父母严厉的话语中感知爱一样。现在我知道,告诉病人坏消息最重要的是确保病人能感觉到你真的很关心他/她。在“消化”了诊断结果后,拉梅什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他的哥哥回到了我的诊所,选择在我们中心接受治疗。我们讨论了他的预后和治疗方案,当我在浏览副作用列表时,他再次泪流满面。我告诉他,我会尽力帮助他,并本能地把手放在他的背上。他开始哭得更厉害了,他的妻子也在哭。我牢记我同事的建议,并努力表现出“强硬”,告诉他一些更坚定的建议,尽量不表现西方提倡的共情。我告诉他,“想想你的孩子,你是一家之主,如果你这样哭泣,你的家人怎么办?你要为你的妻子和孩子坚强。”这么一说,似乎确实有效。拉梅什停止了哭泣并感谢我,承认我对他说的是真的,并保证他会尽力为家人保持坚强和积极的态度。在之后的治疗中,他的妻子也感谢我。这种方法与我在西方接受的培训完全相反。如果你在西方国家工作,你让哭泣的病人别哭,那你的“饭碗”可能有风险。但这种方法在尼泊尔似乎行之有效,因为同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最重要的是确保病人感觉到你对他/她的真正关心。日本文化不同于尼泊尔和北美。在日本,在住院癌症病人的床边看到诸如名字为《什么是死亡》、《死亡是新生命》等书籍并不稀奇,因为他们讨论死亡并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忌讳。在日本,通常我会为病人提供临终问题咨询,病人会流泪,但病人及其家人都会向我鞠躬致谢。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那天晚上,我和一位同事讨论了这个话题,问他怎么应对这种情况。他告诉我,病人及其家人希望我们坚强。显然,如果医生表现出明显的同情迹象,病人可能会认为预后要比实际情况差得多。尼泊尔的病人似乎更希望医生用偏“强硬”的词表达他们的关心,就像从父母严厉的话语中感知爱一样。现在我知道,告诉病人坏消息最重要的是确保病人能感觉到你真的很关心他/她。在“消化”了诊断结果后,拉梅什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他的哥哥回到了我的诊所,选择在我们中心接受治疗。我们讨论了他的预后和治疗方案,当我在浏览副作用列表时,他再次泪流满面。我告诉他,我会尽力帮助他,并本能地把手放在他的背上。他开始哭得更厉害了,他的妻子也在哭。我牢记我同事的建议,并努力表现出“强硬”,告诉他一些更坚定的建议,尽量不表现西方提倡的共情。我告诉他,“想想你的孩子,你是一家之主,如果你这样哭泣,你的家人怎么办?你要为你的妻子和孩子坚强。”这么一说,似乎确实有效。拉梅什停止了哭泣并感谢我,承认我对他说的是真的,并保证他会尽力为家人保持坚强和积极的态度。在之后的治疗中,他的妻子也感谢我。这种方法与我在西方接受的培训完全相反。如果你在西方国家工作,你让哭泣的病人别哭,那你的“饭碗”可能有风险。但这种方法在尼泊尔似乎行之有效,因为同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最重要的是确保病人感觉到你对他/她的真正关心。日本文化不同于尼泊尔和北美。在日本,在住院癌症病人的床边看到诸如名字为《什么是死亡》、《死亡是新生命》等书籍并不稀奇,因为他们讨论死亡并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忌讳。在日本,通常我会为病人提供临终问题咨询,病人会流泪,但病人及其家人都会向我鞠躬致谢。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个性化医学的实践 告诉病人坏消息和讨论死亡是癌症治疗中最棘手的问题。不幸的是,我们接受的培训不足以应对这类情况。虽然医疗圈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来标准化如何告知病人坏消息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这是肿瘤学。这要求我们真实面对病人,并用既能表现出我们的同理心又不与他们的文化相冲突的方式照顾他们。虽然培训确实有帮助,但在告知病人坏消息时,培训不能解决的最关键要素是:具有同理心和敏感度。知识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但是倾听和真正关心照顾病人必须在经验丰富的导师带领下,将之融入自己的性格中。规则和指南会有所帮助,但是我们服务的病人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提醒我们要保持灵活性,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尊重他们的价值观及塑造这些价值观的文化。讲述不同国家的故事,并不是要说哪一种方式更好。每种文化都不同,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每个病人也不同。我们需要根据病人的文化背景来确定如何告知病人坏消息,这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护理的第一步。对我来说,这是个性化医学的真正实践。每个病人面对死亡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是病人的文化如何影响他们对这种恐惧的反应以及我们作为医生如何根据这些文化差异来调整治疗方法,这是医生行医的美,也是作为一个人的美。原文作者:Bishal Gyawali, MD, PhD, Queen's University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原文来源:Medscape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个性化医学的实践 告诉病人坏消息和讨论死亡是癌症治疗中最棘手的问题。不幸的是,我们接受的培训不足以应对这类情况。虽然医疗圈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来标准化如何告知病人坏消息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这是肿瘤学。这要求我们真实面对病人,并用既能表现出我们的同理心又不与他们的文化相冲突的方式照顾他们。虽然培训确实有帮助,但在告知病人坏消息时,培训不能解决的最关键要素是:具有同理心和敏感度。知识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但是倾听和真正关心照顾病人必须在经验丰富的导师带领下,将之融入自己的性格中。规则和指南会有所帮助,但是我们服务的病人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提醒我们要保持灵活性,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尊重他们的价值观及塑造这些价值观的文化。讲述不同国家的故事,并不是要说哪一种方式更好。每种文化都不同,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每个病人也不同。我们需要根据病人的文化背景来确定如何告知病人坏消息,这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护理的第一步。对我来说,这是个性化医学的真正实践。每个病人面对死亡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是病人的文化如何影响他们对这种恐惧的反应以及我们作为医生如何根据这些文化差异来调整治疗方法,这是医生行医的美,也是作为一个人的美。原文作者:Bishal Gyawali, MD, PhD, Queen's University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原文来源:Medscape文章转载,请关注“健康界”公众号
更多精彩内容,点击“阅读原文”成为健康界VIP,来《看健日报》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