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者必读:一个哲学家的睡眠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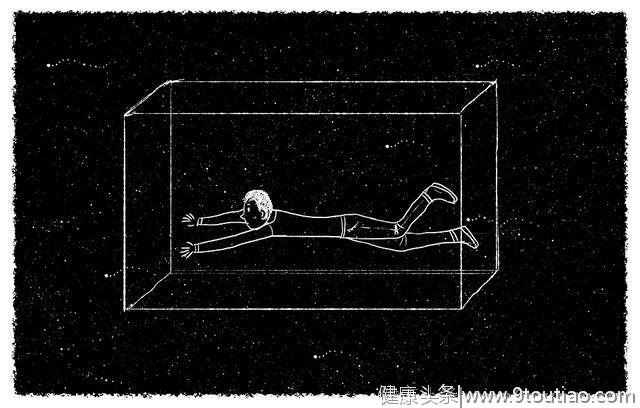
我自己有时也会在读海德格尔时打瞌睡,还有几次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本刚刚翻开的《纯粹理性批判》从我手中滑落。我想,应该不会有比这更深刻的对理性的批判了,不管是纯粹的还是不纯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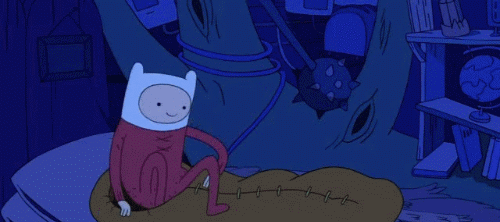
◆一个哲学家的睡眠手记
Note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Sleep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哲学家们都不爱谈论睡眠。如果一个哲学家认为哲学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达到最彻底的清醒状态,那么他就很可能把睡眠当做敌人。当然,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哲学家们去研究这种定时强制我们无法思考的魔咒。
如果我告诉你我患有一种神经病,其症状是每天有八小时或更多的时间会失去对自己各种能力的控制,会与外界完全隔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觉和妄想中——比如在斯托克波特火车站被一只大灰熊追赶——你一定会觉得我的状况非常糟糕。如果我还告诉你这种症状还会传染,你可能就会在祝我好运之后赶紧跟我拜拜。
可这就是睡眠。它根本就不是病,而是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对于这类普遍现象,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睡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每个人都需要在每天的日常活动之后两眼一黑、躺上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事,谁都不会觉得奇怪。简言之,我们不觉得睡眠有多古怪,只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要睡觉。而那些没有“泰利斯氏妄想综合症”的人才是真正令人同情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患有慢性失眠症。
由于所有的动物都要睡觉,我们就认为睡眠是有其生物性目的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有很多理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例如睡眠可以保存能量、促进生长、巩固记忆,或者让我们在天黑后长时间潜伏以躲避外界危险等。
但这些理论无一不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上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快速动眼睡眠(Rapid Eye Mouvement sleep)的发现者之一威廉姆·德门特(William Dement),在经过了五十年的前沿研究后总结道:“我们需要睡眠的唯一理由其实非常牢靠,那就是我们会犯困,会变得想睡觉。”

犯困的哲学家们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哲学家们都不爱谈论睡眠。如果一个哲学家认为哲学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达到最彻底的清醒状态,那么他就很可能把睡眠当做敌人。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睡眠恐惧(Hypnophobia)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尼采曾经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困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安睡。”
他自己还尝试过尽量不睡觉,比如有一次他试着在两周的时间里每天只睡四小时。(当我在七十年代第一次读到这些的时候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那时我还是一名实习医生,每周工作 104 小时,有时还需要 48 小时不间断待命。)
让-保罗·萨特的小说《恶心》中的反传统式主人公罗冈丹,也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自己常去那家咖啡馆老板的厌恶之情:“当这个人独自待着的时候,他就昏昏欲睡。”
萨特另一部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也曾惊恐地发现,火车上他对面座位上的人睡着了之后,会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机械地随着车厢晃动的节奏左摇右摆。
当看到人的生命在没有自我意识的状态下的延续,当看到鲜活的生命进入半死不活的昏沉状态,我们就会意识到,生命中种种有意识的选择,其实基于这种无法选择的自我延续。
睡眠不仅会让人看到人类终极的无力,还让人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中,思想的位置是多么有限。
此外,它还会引发对传染性的恐惧:一讨论睡眠好像就会引人入睡一样——我们现在一提打哈欠,有百分之五十的读者就会在十五分钟内打哈欠。(这是说真的!)
当然,没有什么理由禁止我们的头脑去思考它的对立面,也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脑力超群的哲学家们去研究这种定时强制我们进入无法思考之状态的魔咒。不过在这方面贡献良多的其实是物理学家们,因为他们把超群的智力用在研究这种现象本身的性质上,而不去考虑睡眠对他们自己的意识有什么意义。
而哲学家们还得特别去担心他们自己的作品可能带来的催眠效果。藉由那些精心设计的论证和不厌其烦修改过的句子,他们希望能够揭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面貌。可事实上哲学作品比漫画书和八卦杂志更容易让读者把世界抛到一边而去打个小盹。
一些更为坦率的哲学家则承认不能抱怨这是把哲学的珍珠扔在昏猪面前(典出《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曾经在更伟大的哲学作品面前犯困。
我自己——作为一个小角色——有时也会在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打瞌睡。这本书可算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十年前我还写过一本关于它的专著,而这本专著可能也曾让不少人睡过去。
还有几次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一本刚刚翻开的《纯粹理性批判》从我手中滑落。我想应该不会再有比这更深刻的对理性的批判了,不管是纯粹的还是不纯粹的。
对于笛卡尔来说,停止思考就意味着“我”不再存在,所以睡眠会让思考停止这种事着实让人头疼了:它意味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不是连续的,而是被这种植物性、器质性的时刻隔断的。
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在他的文章《睡眠哲学:笛卡尔、洛克与莱布尼兹》中指出,笛卡尔把心灵看做一种实体,因而心灵的活动——也就是思考——必须是连续性的,不能有任何间歇。
如果心灵可以一会儿被讲师的声音打断、一会儿又被鞭子抽醒,它就会被偶然的属性改变,从而算不上是一种实体。由此,笛卡尔认为即使在最深的睡眠中我们也不会停止思考。可问题是我们对深层睡眠中的思想没有任何记忆,这是什么特殊情况么?
约翰·洛克则不这么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在睡眠时我们不思考,这就是事实。“每一个盹儿都动摇着笛卡尔的学说。”
莱布尼兹则试图为笛卡尔辩护。他的论据是后来弗洛伊德理论的雏形:我们在无梦的睡眠中也会思考,只是这些想法都是无意识的,这有点儿像我们不经意地看到什么东西,但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看到了什么。我把这场争论留给读者去仲裁。总之,这些理论的不足之处是另一个让哲学家对睡眠问题望而却步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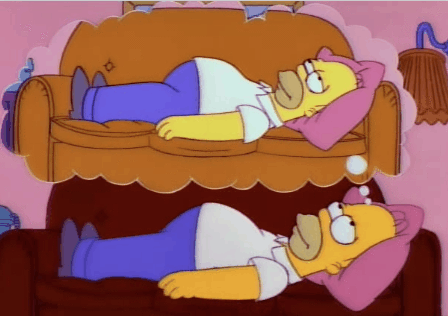
做梦
在哲学中,梦的地位要显著得多。由于做梦是某种形式的有意识状态——亚里士多德就承认“灵魂会在睡眠中给出意见”——它就比纯粹的打呼噜高了一个层次。
更重要的是,梦境让我们在哲学意义上对周遭的世界产生了怀疑。当人做梦的时候,梦境的真实程度可以跟你阅读这篇文章的体验(也可能就是打盹儿)相媲美。
笛卡尔在他的《沉思录》中就写到:“没有任何确定的证据可以让我把清醒状态和梦境区分开来。”当然我们可以取巧地回答他说:我们不需要去寻找这种“证据”,因为我们并不据此来判断自己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可是我们内心的哲学冲动不会满足于这种答案,因为它想要(或者装作想要)或需要(或者看起来需要)找到这样的确定性,于是我们就得孜孜不倦地投身到对确定性无穷的追问中去。
有一种可能性是:睡梦中那个脆弱的、容易轻信的自己会借由梦境——它好像是由自己又好像不是由自己拼凑起来的——来叙述睡眠中的体验,来理解当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几乎与外界脱离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满足对意义的极度渴望,人会为某种感觉配上完整的情境,比如为了解释肢体突然的颤动,我们认为自己是从悬崖上掉下来了。简言之,我们会为了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找到某种意义。
这可能为真实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注脚:任何能够合理化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可能是真实的;反过来,任何让我们觉得是真实的事情,我们都会试图将它合理化——而且成功率惊人地高。
做梦是一个尤其惊人的例子:在梦境中,我们的心灵会区分出一个试图将一切都合理化的“我”和一个被合理化的现实——它真实得甚至可以让我们屏息以待接下来的发展。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创造了泰斯特先生这个角色。在这个“没有神的神话”里,泰斯特致力于不间断、不分心的思考。他全部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杀死木偶”,杀死自己内心的机械小人。
在著名的《同泰斯特先生一起的一个夜晚》末尾,瓦莱里让他的主人公一边渐渐沉入睡眠,一边还观察着自己入睡的过程。在他的自我意识几乎褪尽的时候,嘴里还呐呐自语道:“让我们仔细想想⋯⋯你可以在想任何问题时睡着⋯⋯睡眠可以延续任何思想⋯⋯”瓦莱里坚持了记了五十多年的日记。
这些日记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观察自己醒过来的过程,比如在清晨,他会记录下自己脑子清醒过来的状态。当然,梦境也像每天的自我苏醒一样让他着迷。他认为梦境是意识试图解释身体从睡眠到清醒状态之变化的尝试。
跟我一样,他不赞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所谓梦是“通往潜意识的皇家大道”是没有实证依据的,可是这种靠语词堆砌起来的谬论居然会被很多聪明人看作是科学观念。瓦莱里也不认为梦可以预言,或者说让心灵穿越时空,看到未来或者上帝的意志。
做梦时,意识可以脱离感官世界,自由地编织夜晚的冒险之旅。对做梦者来说,无论是以主角的身份掌控着事态发展,还是无助地处于各种事件的中心,梦境都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不过讽刺的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听一个人自说自话地讲述自己的梦境更让人昏昏欲睡了。这种时候,我们都渴望听到那句魔咒:“然后我就醒了。”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不过我不会了,免得让你从“睡眠哲学”直接进入了睡眠本身……